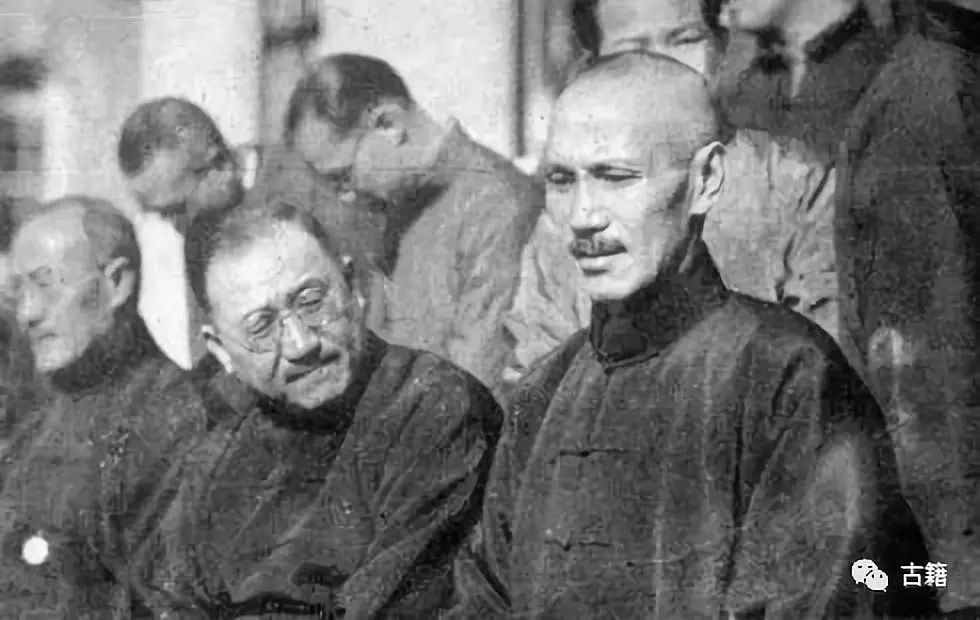六 余论
综观这次争论,可以发现,顾颉刚、傅斯年等人认为是几大种族“混合无间” 而组成了“一个” 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里边包含了汉、满、蒙、回、藏、苗等种族“汉族” 的名称不准确,应该称为“中华民族” ,因为汉族里边已经包含了满、蒙、回、藏、苗的血液而满、蒙、回、藏、苗也只能称作为种族,而且是“中华民族” 之后进者。虽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顾、傅等人的观点都带有强烈的“政治” 意味和时代意味但是,他们的观点也并非全无学理依据。当然,傅斯年顾颉刚在此处还是有所分歧的,傅斯年的主张更为极端,他认为“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顾颉刚则认为“各族间俱有特殊的文化,须求充分的彼此了解。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语言文字的介绍工作。汉蒙回藏四种语文,都是中华民国今日行用的国文国语,不可偏废,蒙回藏地方的学校应以本地语文为主,而以汉文为辅。我们不但要保存当地的语言文字,更要发展当地的文学和艺术,充实他们的智识遗产。”
其实,对于这场争论,撇开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和看问题角度的差异不谈,中国学人的拳拳爱国之情由此昭然可见。当时大量撤退到西南的人文学者发现,西南是民族史与人类学的一片崭新天地,所以组织“西南民族学会” ,兴高采烈地研究这方面的学问。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本着科学的精神,从事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本来也在于弄清西南边疆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 。这也正是傅斯年等人一向竭力倡导的。早前,傅斯年等人组织或支持的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就是有鉴于“西南民族的固有文化,是我国学术上的宝库” ,而且西南民族住在边疆的要区,“在国防上是有重大关系的” ,“若不急起调查边睡的土人及境域,作保护国界的参考” ,可能不久的将来,云南的地图“将日渐变色了” 。但在民族危机四起,边疆为强敌所谋之际,傅斯年等人所遵循的客观征实、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风格不得不作出自我调整。傅氏忍不住痛斥西南民族学会所治的是“无聊之学问” 。顾颉刚也自陈“要对时代负责” 。可见,尽管各人的观点不同,但在加强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可以说,产生这场争论的缘由正是各方都只看到或强调问题的一面,顾颉刚强调的是各族间的一体性和“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 的时代压力费孝通等人却更看重各族间的多元性,向往“和而不同” 马克思主义学者翦伯赞却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各民族间经济和政治的平等。论争各方所关注的焦点正是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关系“一个” 民族组成的国家和“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 ,谁更统一谁更能得到人民的认同而抗日战争时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又让这样的争论有着特殊的意涵。其实,“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 ,学术观点及其盛衰是顾颉刚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把这场论争放在更长程的历史中来审视,当可发现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此时或正回归于以“文化” 区分民族的传统观念,即只要“周边” 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就可以成为“中国人” 而传统民族观念也因此和现代西方民族观念进一步碰撞并不断调适,费孝通多年以后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重要命题很可能受到了这场争论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