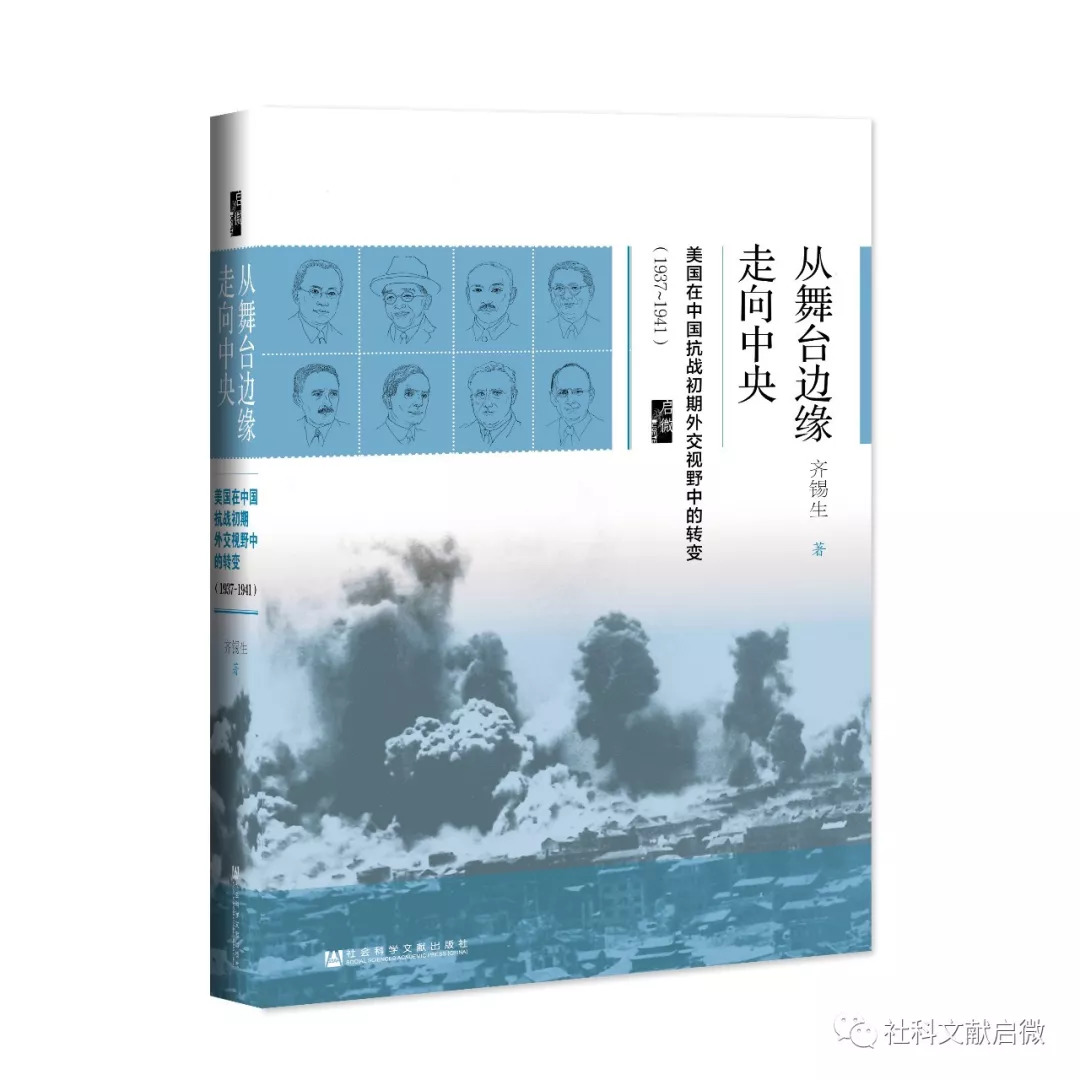关键词:地方;国家;龙云;边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14CZS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金生,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地址: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邮编650050。
1899年,梁启超曾言:“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而“自秦、汉至今日,可直谓为统一时代”;[1]然他亦认为因中国“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结为团体,以自整理也”。[2]钱穆的观察与梁氏相似。1946年,钱穆言:中国自“秦汉以下,郡县一统,集权中央”,然而中国“地大民众,土风习俗,文教材性,南北东西各有不同,经济所宜山川物产,影响人民生活者,亦随地而殊——并认为“西汉初年之大封同姓,东汉末叶之州牧,中唐以下之藩镇”等现象是传统“一统政治下偶有之变象与病态”。[3]钱氏所言的“变象与病态”于晚清时期即是在中外因素交替作用下呈现出的政治区域化形态,而这一形态发展至民国时期则益加明显。[4]民国建立后,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形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以其为核心或中心聚集而成的“西南军阀”这一地域政治势力,在北洋政府时代的政治生态中一度相当显赫。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西南军阀”地域实力派因内外形势的变化,团体色彩逐渐淡化,滇川黔三省的政治走向各异,1935年后贵州及四川逐渐失去“割据一省”的独立性,仅云南尚勉强维持着“割据一省”的政治形态。[5]
20世纪30年代,曾任美国外交政策讨论会主任的别生在分析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形态时就称:19世纪初期,“清帝忽然遇到从未见过的西方侵略。敌人从海道而来,用西方新式机器的技术。从前对付边夷的方法不能来抵御新式和不测的海上杀伐与技术专精的民族”,传统中国的策略无法应对新形态的列强,“反屡蒙其害”。[6]这不仅对近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变革产生了根本影响,更直接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虽结束了北洋政府时代中央政府更迭频繁的政治形态,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处于一种派系平衡中的“脆弱”形态。由于边疆多属交通僻塞、民族与宗教多元的地区,地方政权仍多属于当地军政上层人物控制,西北边疆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诸省,西南边疆的云南、西康、广西、贵州诸地,均为中央政府控制的薄弱区域,地域政治形态及内外博弈十分复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南、西北边疆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西北西南边疆各地,已为吾国长期抗战之根据地,故其重要性愈益明显,吾人更应有密切注意之必要”。[7]云南因护国、护法运动中的表现,其在边疆诸省政治形态的发展变局中,颇具一定的独特性,故观察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龙云在1937抗战爆发前后的言行,对于审视地方实力派在全国性政治动员中的表现,思考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局中的边疆政治形态诸问题,或有裨益。
一、他者的观察:1935年蒋介石入滇之行及其对龙云的观感
1935年1月31日,蒋介石在其日记的本月反省中写道:“滇龙效忠中央,当信任之”。[8]此时正值蒋介石急于部署兵力围剿进入西南地区的中央红军,强调应当信任龙云对中央的效忠态度,但事实上或正表明其对此之疑虑。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蒋介石既面临着国民党高层内部激烈的政治及权力博弈,又面临着地方实力派存在的挑战,西南一直是其未能有效控制的区域之一。正如有研究者观察到的那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西南诸省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但实际上却为地方实力派控制,国民政府对他们也大致是采取怀柔、笼络之策,双方维持着脆弱的和谐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龙云在“联桂”与“拥蒋”之间选择了后者,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派兵进击广西,但龙云此举,并非为真心“拥蒋”,不是“基于国家利益或是主义信仰”,主要是根据自身现实利益而决定的。[9]不过,1935年,蒋介石借追击中共红军之名,指派薛岳乘机入据贵阳,解除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职权,实现了对贵州的直接控制。滇、黔地理位置接壤,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历来唇齿相依,蒋介石借假途之机,将贵州吃掉,龙云产生唇亡齿寒之感,对蒋自然戒备。[10]然而,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首次抵滇视察,与龙云第一次见面,双方之观感却甚好。
1935年5月10日,是蒋介石入滇之日,其预定之事有:“与龙云商西南及贵州大局”、“商云南交通与军事”。[11]11日,预定的事也是“与志舟(指龙云,引者注,下同)商议西南问题”。[12]蒋介石与龙云如何商议西南问题之事,目前尚未见具体史料,但根据蒋介石11日的日记中言,本周与龙云商议各事,包括两广方针、贵州方针、西南公路、云南军队番号与委任、经济建设等。[13]自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虽然与日本关系时紧时缓,蒋介石应付时局的具体策略也不断调整,但为应付国际局势尤其是“倭患”问题进行部署,却是蒋介石一直没有放松的政治方略。此次蒋介石云南之行时,正值华北形势日益严峻,“倭患”早已成为蒋介石日益思索的主要难题,其与龙云之会谈虽可能仅谈国内的具体问题,但亦应当涉及“外祸”。蒋介石在云南的诸多言论,事实上正是因应“倭患”而发。
5月1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参加宴会,即席发表演讲。蒋介石的讲话包括以下内容:一、“此次来滇,已将中央的精神带到云南来,和云南党政军各界各同志以及云南全省同胞的精神团结一致,而且一定能够将我们云南全省民众的精神带回到中央去,使云南全省民众的精神与中央的精神整个彻底的团结起来,共同担负国民革命的责任”,虽然目前不一定可以见到多大效益,但是一定在最近将来发生最大的效果。二、“希望我们云南同胞要大家起来建设一个真正工业化的云南,来作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开发富源、振兴工业,是我们挽救希望复兴民族急不容缓之事,云南蕴藏丰富、土地肥美、气候温和、民性勤俭,是一个最好发展工业的省区,一定要在云南建成坚实宏大的工业基础,才可以复兴我们的民族,云南对于国家和民族有着重要的责任。三、来到云南后,“对于复兴民族的志向,更加坚定,而且实在增加无穷的希望”。只要团结一致,“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设成工业化的云南,作复兴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蒋介石表示中央与地方应团结一致,虽有示好、笼络之意,但建立工业基础以复兴民族之说,实是抗日的一种部署,针对日本的色彩很强:“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是农业国家,其心目中所谓农业,即是认定我们一切落后,应当要作他们工业国家的奴隶,不配和他们讲平等。”[14]蒋介石所谓的“外国”虽未明言,但结合当时形势,主要应指日本。蒋介石在1934年及1935年先后视察了中原、西北及西南地诸地18个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防御日本做准备的。是故,蒋介石此次昆明之行,虽然名义是为了部署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但也未尝不是为了落实他1932年就提出的“救国之道,不可忘却基本区域”思维,为抵御日本进行部署。[15]然而,蒋介石预定在3年内将云南建设成民族复兴的基础地,事实上2年之后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云南在抗战中的表现与作用也更加突出。
5月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的“注意”事项写道“倭寇与桂逆勾结”。[16]13日,蒋介石在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会议上进行讲演,题目为《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主要内容的表述虽与12日的即席讲话有所不同,但主旨也是强调云南社会各界“格外要奋发努力,团结精神,来领导起全省的同胞,共同一致来建设新云南,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17]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防政策与外交政策无论表里精粗,亲疏远近,皆应以倭为中心也”。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记载了当天他与龙云进行的第一次长谈,虽然长谈内容笔者尚未见到具体材料,但龙云却给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志舟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18]根据上述观察,可以推断蒋介石当日与龙云之谈话,内政自是必然,应当也涉及对日问题,并可能谈及他计划抵御日本的一些部署。龙云对蒋介石的部署与计划应该是表示了相当的支持,是故蒋在日记中才会对龙给予较高的评价。龙云对蒋的支持内容,自然应包括了蒋的“抗倭”计划与部署。5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的“注意”事项即写道:“桂白(指白崇禧,引者,下同)介绍土肥原倭寇使者来见志舟,威胁志舟附白叛乱,其言之暴蛮,直不视中国为有人,幸志舟拒绝,而使其副官代见也。呜呼,桂倭之肉不足食矣。”[19]从日记中所写内容来看,蒋介石对桂系与日本的联系深以为恶,但对龙云拒绝亲自会见日本密使的行为满意。龙云的这一举动,自然是对日本引诱的拒绝,也是支持蒋介石的表现。
5月18日,蒋介石与龙云在晚上谈了两广问题,在日记中的“本周反省录”写道:“倭寇骄横忤蛮污蔑,无所不至,应切思之”;“志舟相处益,此来后民众信仰倍增,结果对于国家前途之关系实大也”。[20]此时,对国家与民族威胁最大者,自然是日本。蒋介石因与龙云的相处感觉融洽,而认为此事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十分有益。这表明二人对“抗倭”问题是有共识的。5月19日上午,蒋介石对昆明中等学校师生训话,其题为《为学作人与复兴民族之要道》,其主旨也是要求云南同胞“要担当起复兴民族的责任”。下午两点半,蒋介石乘坐飞机,由昆明经过富明(今富民)、元谋、金沙江、会理、永定营,直至德昌、西昌,然后再向东经普格、披沙、巧家,最后返回昆明。在日记中他感慨道:“沿途土地肥美,到处皆有水田、森林,人烟亦不稀少,道路亦甚平坦,实与未见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华地大物博,何处皆可立国图强,倭寇必欲急急灭亡我国者,其果能乎?适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21]蒋介石在云南无时不思“倭患”,乘飞机巡视云南各地后的感慨,说明云南是民族复兴重要基础的想法在他心中更加坚定。而这种坚定,也来自他与龙云见面后双方在政治行为上达成的共识。
5月20日下午,蒋介石和龙云一起到了龙氏在昆明西边的海源别墅,并游览了筇竹寺。在日记中,蒋介石记道:在海源别墅时,他“告其(指龙云,引者)对两广方针,与注意之点,及政治主张毕”。[22]蒋介石告诉龙云相关政策后,龙云的反应不见记载。不过,21日的蒋介石日记则说明龙云对蒋的计划是支持的。5月21日,蒋介石离滇。当日上午,蒋介石会见了云南各厅长,并作了训示,与龙云谈话,然后照相留念。正午时,送宋美龄至滇越车站登车后,蒋介石即转到巫家坝机场,龙云与蒋同车抵达机场送行。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以时间过早候机不到,送行者劳等三点余钟,志舟主席几病,心甚抱歉”。[23]至此,蒋介石的云南之行终告结束,而在离别之时,对龙云因送行而几乎生病而“心甚抱歉”,结合前面对龙云的较好观感,可以看出此时他对龙云的态度是非常亲密的。按照陈布雷的回忆,此次蒋介石与龙云见面后,龙云对蒋十分钦佩:“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指陈布雷,引者)等言之者再”;蒋介石也称赞龙云“坦易而明大义”,只与龙云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地,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示,蒋公均仅示大概,属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与速效焉”。[24]陈氏的回忆或有蒋、龙双方特定政治场合的表现,但蒋介石日记中对龙云此时的评价,说明了蒋此次云南之行,达成了他的政治目标,既取得了龙云在“围剿”中央红军、对桂等内政问题上的支持,也应取得龙云在“倭患”问题上对蒋介石的的支持。
1935年农历的6月1日,龙云在给两广陈济棠及李宗仁的电报中,言及蒋介石云南之行,并对双方关系表示了劝说之意:“介公(指蒋介石,引者)在滇时,对于时局有所垂询。盱衡大势,国家地位危险如此,再不亟谋统一,结果国即灭亡;若不互见以诚,统一亦终难实现。沥陈之余,介公颇为动容,有极诚恳之表示。谋所以弭内争而御外侮者,正此时也。介公既表示真诚,遵意未识若何?”[25]龙云之电文虽然委婉,但却表现了对蒋介石“弭内争而御外侮”的“真诚”态度的支持。结合前述相关论述,龙云应该认识到蒋介石的云南之行是对内统一与对外御侮的部署考察,他亦表现了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当然,龙云与蒋介石的这一融洽关系,并非是完全的“亲密无间”,更多是时势条件下的政治选择,国民政府中央无法实质控制云南地方实权,而龙云也需要在中央认同下求得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关系自然会产生变化。[26]
二、“皆国家之力”:龙云在抗战爆发后的言行
不及蒋介石所期望的云南3年工业化建设顺利完成,1937年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这对中国政局演变产生了根本影响,也使中国的边疆政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西北为抗战根据地后,“开发西北”之社会舆论高耸入云。[27]当时国民政府以西北为抗战根据地,社会舆论也广泛重视西北开发建设,天津《大公报》的一篇社论颇能道清其时西北、西南边疆政治的复杂性。社论言:“最近国人注意西北事,似较前殷切。……此亦政界目光趋重西北之一证”,九一八事变后,国家为固本自卫考虑,必须经营后方以备不测,“故西北建设,在今后尤为重要”。但同时,该论也称:“吾人日前论川事,以为四川亦中国最后之堡垒,故属望四川军人觉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尚未定,中央政令,犹不通行,故宜暂作别论。至于西北数省,则中央政令,完全贯彻,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为之主持”,认为“四川难治,而西北易治”。[28]从国家中央政治的层面考虑,该论观察到此时西北、西南边疆与中央政府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被消解,而“西南军阀”这一地域政治势力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之后已经分解为以省域为范围的地方实力派[29],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央对西南的控制依然相对薄弱。国民政府中央以西北边疆区域为抗战的根据地,不能不考虑对西南边疆社会政治影响较弱的这一现实因素。不过,在1935年后,伴随中央参谋团入川、贵州军政改组,国民政府对西南的影响增强,是故蒋介石才决定迁都于重庆,西南边疆在政府及社会的各界的视野中才又受到重视。前述蒋介石云南之行,正是西南边疆政治形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变的重要过程。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7月17日发表演讲,称:“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祗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30]在7月底平津失陷后,国民政府决定于8月7日举行国防会议,共商抗日大计。虽然当时各地将领都发出通电,表示拥护中央,不过据李宗仁回忆,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初,事实上龙云对蒋介石能否坚持抗战是心存疑虑的。李宗仁回忆称,在七七事变后的四五天,蒋介石就从庐山发电至桂,约其与白崇禧速赴庐山共商抗日大计。在双方电文往来过程中,龙云有所听闻,并来电劝阻其与白崇禧赴京。龙云劝阻的原因,是认为拿不准国民政府中央作战的诚意如何,担心李、白入京后,“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龙云为何担忧李、白此时的态度呢?原因在于他认为蒋介石为人尚于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李、白扣压,则广西就必为蒋系控制,这样“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则将岌岌可危。”这说明,此时龙云之思考尚是从维护地方政治利益的视角而出发。[31]此亦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龙云系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之嫡系,龙云与蒋介石二人之间并不存在信任,更谈不上亲密;龙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政治的需要,在上台初期不得不追随蒋介石。但是,作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龙云又不可能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他“也把云南视为自己当然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不允许旁人涉足”。[32]前述李宗仁回忆龙云劝阻其赴京之行为,正是这一考量的结果。不过,最终在抗日民族大义之下,龙云还是赶赴南京。此或表明,在维护地方政治势力与国家利益之间,龙云选择了后者。[33]
在8月2日,龙云发给蒋介石一封电文。电文称:时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表示云南地广人稀,本来“对于壮丁之调用,困难实多”,所幸近年来云南部队及团防都试行着征兵制度,实行退伍,到本年年底,退伍士兵约在10万左右;如果对日全面战争开始后,拟请中央不要零星调动云南部队,云南可以组织6万至8万之数,组成建制部队,由他亲自率领或开往前方增援,或者在长江沿海一带布防,等战争结束后,再一并解散归农,不会产生任何问题。龙云表示,他这样的行为“一则了誓为国牺牲之愿,一则以报钧座(指蒋介石,引者)德恩于万一”,如果蒋介石同意,应请着手办理,这样至本年冬季“始能出动”,并强调相关一些具体问题,“容后到京面谒陈述”。[34]蒋介石接电后,回复称龙云“忠贞谋国,至深赞佩”,表示对龙云的相关请求已经令军政部统筹办理。[35]此时,龙云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抗战态度并不清楚,他之所以愿意赴京,一方面既是基于国家大义的考虑,一方面也是其时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通过赴京了解中央态度,可以决定下一步之举措。8月6日,被龙云派到滇东北尾追中央红军的孙渡发电称“顷闻钧座(指龙云,引者)日内飞京,在目前时机实属必要”,现国难严重、存亡所关,在敌强我弱态势下,应“把定大战常理纯粹抵抗之原则,发挥等待战争长期疲敌,使敌渐感其不胜用力之多,而后能胜敌”。[36]对此,龙云回电称:“国难严重,而中央内容不甚明了,故亲赴京一视,在京不久延,数日即归。纵队部(指孙渡所属的第三纵队,引者)应俟史华回榆后,弟(指孙渡,引者)再晋省面详一切可也”。[37]在准备充分后,龙云于8月9日抵达南京。
这是龙云掌握云南地方最高权力后第一次入京,受到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据龙云回忆,他从昆明先飞西安,而后经武汉到达南京。到达南京机场时,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同何氏乘车到北极阁宋子文家中食宿。11日,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当天就邀请龙云共餐,汪精卫、冯玉祥、丁惟汾等要人亦在场。[38]8月13日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日军空袭南京,蒋介石派遣侍从来到龙云住处北极阁,以北极阁目标太大、不安全为由,安排龙云住至汤山。当龙云从汤山返回北极阁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亲到龙云住处,双方进行了范围很广的谈话。龙云回忆称,蒋介石与其谈话的要点是希望云南能出两个军的兵力抗日。龙云当即表示可以办到,但只能先出一个军,另一个军则要视战争情况而定。蒋介石得到龙云的肯定答复后高兴地言:“一切供应和补给,我告诉敬之(何应钦)同你商量办理就可以了”。蒋介石还问及龙云对当时军事形势的看法,龙云认为上海淞沪战事恐难持久,若上海有失,则南京亦受威胁并难以固守,国际交通也将困难。蒋回答称若出现此种情势,“只有从香港和利用滇越铁路到达内地”。龙云判断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大举进攻上海,其南进政策必付诸实施,若南方战区扩大,香港与滇越铁路将受到威胁,建议应该在国际交通方面早作准备,应即刻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可由地方负担、中央补助,而铁路则由中央负责、地方协助。蒋介石对龙云的建议甚感赞同,表示将令交通部、铁道部与龙云具体商议。[39]而在8月12日、15日,龙云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了支持中央抗日的态度。12日,龙云在出席川滇旅京同乡联合欢宴时表示,为争取民族生存,准备抗战到底,称“滇省军队早经整理就绪,随时皆可为国家而效命也”,云南“为国家贡献能力无机会,护国而后,今其时矣!”15日,龙云会见云南在原南京中央陆军炮兵学校的同学代表时表示:“自发生芦沟桥事变以来,我观察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决非一般性侵略,不会以夺取几个省的土地为满足,而是企图亡我中国。我此次进京的目的,不仅符合您们请缨抗日之志,亦代表云南一千三百万民众表达爱国护国之赤诚及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牺牲到底。……大敌当前,必须举国上下一心,团结御侮”。[40]龙云的这些言行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及云南的责任是作了充分思考的,表现了地方意识服从国家大局的认知。
龙云回到昆明后,随即召集云南地方军政负责人,传达其在南京所见所闻,表示抗战再所难免,开始进行抗战的相关部署。[41]8月28日,龙云接何应钦来电。电文称:“前奉委座(指蒋介石,引者)交下吾兄(指龙云,引者)冬机电,建议就滇省退伍壮丁征集六万至八万之数,组成建制部队增防前方,饬核办一案。当以中日战端已开,他日全面作战,自需巨量兵员补充。惟我国现役陆军为数不少,若一旦骤增六万至八万之庞大建制部队,饷糈器帜,急切均难等拨。……滇省退伍壮丁,似可转令作为□□补充野战及后方补充营之用。”[42]何应钦作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高层军事将领,改变之前蒋同意龙云将云南退伍壮丁组成建制的建议,应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商量,此或说明之前蒋作为国民政府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其对龙云当时组军建议的同意,可能是对龙云抗日态度的肯定,是从战略层面而论,对具体的战术部署应尚未考虑完备,而何氏与其商议之后,从饷糈缺乏的具体问题考虑,才认识到增加云南六七万之壮丁为正规军事力量,力有未及。不过,这反而从另一层面说明了龙云对抗日的积极态度。
事实上,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问题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为国人所共同关注,龙云作为一省之实力派,自然不能不虑及于此,并且他对抗日问题有着较深的认识。9月4日,他建议蒋介石应将所有精锐部队及重要武器分期使用,明确判断认为“中日战局,就管见所及,以持久战于我方有利”,担心若在初期阶段所有精锐部队及重要武器就尽量使用,则“后难为继,顾虑殊多”。[43]龙云的这一建议得到了蒋氏赞同,表示“所见极佩”。[44]然而,战事很快发生变化,之前何应钦对龙云主动组军作战表示委婉之意,此时蒋介石却急切希望“滇省军队,务望从速出动为盼”[45];蒋介石在9月5日时甚至表示“兄(指龙云,引者)部何日出发,务望于下月中能集中常德,如何?盼详复。”[46]战事变化莫测,对于蒋的焦急催促,龙云回答称其“回抵昆明后,关于出师,即筹画人员武器之补充与人事之调整,已有端倪”,本来“自应遵照,迅速开拨,用赴事机”,不过在军需军械物品筹备、部队官兵饷用、交通运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困难,希望中央补助。龙云同时强调:“此次出师,滇省所有武器,虽由地方购买,然皆国家之力”,除经费略有不逮外,武器等皆悉数携出,包括法国制造的朗德八一口径迫击炮及哈乞开斯十三米立二小钢炮两种较先进的武器。[47]客观而论,龙云此论与云南地方实际情况尚相符合。他于10月9日给卢汉的电文中充分说明了此点。电文称:“抗日问题,早即料有今日。故于委座两次莅滇之时,曾面呈将来抗日应需滇军参加否?承答云:恐用不着。迨今年兄(指龙云,引者)入京,见情势紧张,亦曾建议滇省可添练六万八万或十万,宜先筹划,以备不时之需,事毕负责解散,乃未蒙军政部采纳。继而突命出兵。此次马上组织六十军出发,已属竭尽心力。但若需要,再出十二团,亦尚可能。惟除此十二团及六十军之陆续补充外,如尚需多兵,则事前毫无准备,一时恐来不及。须请[中][央]指示方略,方能办理。特电知。”[48]揆之龙云与卢汉之关系,此电文之内容可谓是龙云对云南参与抗战行为的真实态度与思考。从这一电文内容可以观察出,龙云主动提出组织军队出滇抗战,这一行为是在个人、地方与国家利益纠葛下的政治选择;电文内容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前面所引的其回答蒋介石称云南军队出滇在经费上存有困难的真实性。
由于龙云对抗日问题早有思考与准备,故从南京回来后,很快就将云南地方部队组建成一军,即六十军,军长由卢汉担任,下辖三师。六十军于9月底组建完成,10月8日开始由曲靖、昆明分头出发,经贵州入湖南参与抗日作战。[49]地处西南边陲的滇军的这一出军速度不可谓不快。而云南军队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各方好评。11月7日,已抵达南京的卢汉向龙云报告了各方对滇军的评价及上海战情,其中包括:(一)各方均谓滇军素质优良,装具完全,具有相当训练;(二)上海方面,我方运动困难;(三)龙云曾电告中央,如前方需要滇军所存弹药,即运京应用。蒋介石接电后,将电文发交各部传观,称“滇省素称贫瘠,能有此存储,深为惊异”,称赞龙云“公忠体国,光明磊落之态度,尤为全国所仅见”。[50]上述表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对抗日行动是相当支持的。
三、边疆与国家建设: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政治隐义
1932年,时人即言:“立国之要素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权,三者莫不相辅而行。土地者滋生之所自,亦即民生之所赖也;人民者,种族之所存,亦即民族之所本也,[;]主权者,人民之所属,亦即民权之所归也”。[51]伴随晚清以降西方力量及学理在中国的强势导入,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国人的疆域、国家主权观念日益明晰。[52]在此形态下,边疆问题逐渐广受关注。而如1930年华企云所言:“自列强对华发生关系以来,形势骤然一变”,形势之变表现为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扰。俄国“始则以尼布楚、爱珲、北京、塔城、诸条约取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外蒙新疆沿边之地”;英人“初藉东印度公司之力,蚕食五印度,收服阿富汗、尼泊尔、哲孟雄、不丹诸国”,而与我国西藏为邻,继又并吞缅甸而窥伺云南之片马及江心坡等地;法人自占领越南以后,“复以英国有谋展缅甸铁路之故,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先设滇越铁路以擅云南之利;不仅俄、英、法等西方强国,东方之日本也对中国虎视眈眈;这使“吾之边鄙也,而被列强侵之”。[53]列强对中国边疆之侵逼,对中国之疆域主权造成严重危机。
或如时人所观察到的,“中国差不多自有历史以来,就有所谓边疆问题”,然古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产生,“或因为汉民族的对外的武力征服,或因为四周的经济较落后的民族的入侵、冲突、接触发生,便惹起较严重的边疆问题”。但是,彼时的边疆问题,“只是民族间的关系,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的问题”;而现在的边疆问题却不是那样的简单,也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仅是边疆国防或边疆开发,“现代中国的边疆问题与过去的和别些国家的边疆问题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与帝国主义有关,更明白地说,他是世界侵害与再‘分割’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边疆问题持续恶化,“不特中国的地图更要缩小”,而且“整个国家恐也不能苟延残喘了”。[54]边疆与国家领土主权、国防、发展诸问题联系益加密切:就领土与边疆之关系而言,“假使边疆有失,中国尚能有发展之余地乎”;就人口言之,“内地人满为患,边地空虚异常”,“若能移密就稀,相互为用,则可普利全国”;就国防言之,边疆为国家之屏敝,“保而有之,则中国安宁,一旦失之,则中国不得安息”。[55]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边疆问题“就是中国的存亡问题”。[56]然而,如前曾述,自晚清开始呈现的政治区域化景象至民国时期更加激烈。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内部派系冲突激烈、权威不振,地方实力派争雄割据,外部国际政治形势恶化、帝国主义侵略加剧,边疆问题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占据主要地位,甚至呈现出一种边缘形态。[57]徐益棠就曾观察言:“中华民国成立至第十九年,内战方告平息,然其时,京粤两方尚因政治意见不合而有争议;四川尚为一大小军阀割据之局面;而红军方力争地盘,自出政令;中央因谋内部之团结,注全力于整军齐政,以谋各方之协调,心目专囿于一隅,故未尝措意于边疆也。”[58]此即是对边疆问题在政府视野中居于边缘地位的另一种客观表述。不过,伴随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边疆政治形态亦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1931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称:“现在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东北对俄问题,第二个是解决西北叛逆的问题,第三个是西南[59]叛逆张发奎的问题。”[60]戴氏所言虽非专论边疆政治形态,但却从另外一个维度说明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葛仍然严重。受制于此,此时国民政府对边疆地方政权的实际控制能力较为有限。前引1933年8月1日的《大公报》社论言西北政令贯通、“盛世才与马仲英,皆听合于中央”,并非西北边疆的真实政治形态,此时甘肃、宁夏、青海的各实力派都与国民政府中央维持着相当微妙的平衡关系,国民政府在新疆的影响则更为薄弱,而社论观察到四川地区“中央政令,犹不通行”的情形,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控制的薄弱。[61]事实上,前述1935年蒋介石云南之行,既有“剿共”的因素,亦有借机观察西南边疆诸实力派政治态度的考量。其时,国民政府虽然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将中央力量渗入西南,但远谈不上强有力的影响或控制。虽然1935年蒋介石的云南之行对龙云观感颇佳,但事实上却是中央势力无法进入云南下的一种无奈的“笼络”,双方彼此并不信任,国民党在很长时期内,在云南的根基是相当脆弱的。[62]龙云之子龙绳武就曾称龙、蒋关系:“老太爷(指龙云,引者)和蒋先生(指蒋介石,引者)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们两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爷认为蒋是一个已经形成气候的领导人物,所以支持他”。[63]但如同前述,抗战全面爆发,事关国家、民族命运,而国民政府已确立以西南、西北边疆为抗战之后方根据地,如此形态之下,边疆地方实力派此时的政治态度与选择对抗战进程发展之影响极大。
龙云在抗战爆发前后关于抗日的相关言行,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边疆地方实力派在国家、民族与地方利益之间的政治选择。时人在1937年的9月18日曾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这外患和内政急剧的变动的六个年头当中,中华民族是遭受到从未有过的厄运。它逐日在死亡线上挣扎,国土也日在无开中缩小”;然而,这6年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却表现出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相继不断的内战”,这是帝国主义采用“以华制华”的方法来造成中国内战的,以使中国不能团结,以便他们顺利侵略;一是“割据的形势”,帝国主义认为割据的形势会“削弱中央政府的威信”而有利于其侵略,遂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扶植地方政权,“使之不能统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不能立即发动全面抗战,与此有很大关系;一是“亡国灭种的危机加紧”。我们一方面在进行着不断的内急与割据,一方面敌人又在加紧进攻,“亡国灭种的火焰在每个国人的眼面前燃烧着”。不过,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则有了很大转折,表现为:一是“和平统一的完成”,“中央政府达到从未有过的巩固”;二是全面抗战的开始,“全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在成千上万的拥到前线去,……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内部统一,才有今日的抗战实现”。[64]上引所论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态及七七事变后全国政局的变化,明确指出“割据的形势”是影响国内及抗战形态演变的关键,而龙云这一边疆地方实力派在七七事变前后的言行及其政治选择,也正是时论所称的“和平统一的完成”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前方战事失利,卢汉希望尽快补充滇军在前线的兵力时,龙云表示了积极支持。龙云认识到“南北战区,先后失利。影响之大,已不可思议”,表示不管军政部对军费如何办理,云南仍将积极准备,观察到“现观时局,华北恐已非我所有,长江亦非安全之地。惟西南各省,可以支持耳”,并分析西南各省中,“粤自顾不暇;桂则嚣张成性,外强中干;川则多头,毫无基础;黔则一无所恃;湘虽大有可为,惜无军权在握。如滇健全者已属寥寥”,表示“今后责任之重,滇人当无法避免”。[65]龙云对时局之观察是洞彻的,并且也表示了在此国家危机下云南的重要责任与担当。12月23日,在中国军队于前线战争中严重失利的紧急形势下,龙云电告蒋介石,希望“钧座坚持既定政策,贯彻始终,诚为目前之惟一救国途境[径]”,表示“凡我中央各领袖,遇有言论时,均须依照钧座持久抗战之意旨为归宿,勿稍分歧,方能步调一致”。[66]这些言论表明了龙云明确的抗日态度。
李剑农曾强调“一切历史事变都是难于斩然截断的”。[67]近代以来,由于内外因素的交替作用,虽然国家一直外患频仍,但内部权势的相互纠葛却从未中断,甚至出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凿枘”、“有统一形势无统一精神”[68]的政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统一了全国,但对地方实力派之约束或控制仍相当脆弱。1935年蒋介石入滇虽然表现出其与龙云关系甚为“融洽”的面相,但双方之关系并非常态政治场景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彼此内心并不真正信任;此时,双方关系属于国内权势者之间的博弈或折冲。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引发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此与内部权势者之间的博弈不同,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面对外来侵略者之时,中央执政者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命运、政治利益关系达到了空前的密切,前引龙云所言云南地方军事力量“皆国家之力”的论说,正或是这一密切关系的另外一种表述。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原来国民党控制较为薄弱的西南、西北边疆地区迅速成为大后方,此时边疆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前途影响极大。因此,前面曾论的龙云在地方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选择了服从国家利益的需求,正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组成,对抵御外敌之意义不言而喻,是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密切关系的另一维度的重要表现。
注释:
[1]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年),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71页。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22页。
[3]钱穆:《政学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0、106页。
[4]参见段金生、贺江枫:《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
[5]参见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6][美]别生:《近代中国边疆宰割史》,国际问题研究会译印,出版地不详,1934年,第3页。
[7]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委员会编印,1942年,第1页。
[8]《蒋介石日记》,1935年1月31日,“本月反省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手抄本。
[9]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年,第199-200、255-256页。
[10]龚自知:《抗日战争前龙云在云南的统治概述》,《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1]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10日,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48页。
[12]《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1日。
[13]《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1日。
[14]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12日,第53-59页。
[15]《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5日。
[16]《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2日。
[17]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13日,第64-65页。
[18]《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3日;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13日,第63页。
[19]《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4日;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14日,第82-83页。
[20]《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8日。
[21]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19日,第94-124页;《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9日。
[22]《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20日。
[23]《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21日;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1册,1935年5月21日,第131页。
[24]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103页。
[25]云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588-589页。
[26]参见段金生:《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政治区域化场景下的边疆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的第1期。
[27]关于这一时期边疆学术研究与时势的关系,参阅段金生:《学术与时局: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西南边疆研究的转承起伏》,未刊稿。
[28]社评:《应尽先注意西北问题》,《(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日。
[29]参见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30]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85页。
[3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桂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6-517页。
[32]张增智:《龙云如何走上反蒋拥共的道路》,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丛刊》第4辑,1985年印,第48-49页。
[33]台湾学者杨维真也持这一观点,认为“因基于民族大义及全国人心的趋向,加以李宗仁等人覆电勉其拥护中央,参加抗战,龙云才一改迟疑不决之态度,毅然赴京与会”。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154页。
[34]《龙云恳组建制部队亲率开赴前方电》(1937年8月2日),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内部印刷,1995年,第1页。
[35]《蒋介石复电》(1937年8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第2页。
[36]《孙渡拟随龙云赴南京电》(1937年8月6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37]《龙云复电》(1937年8月7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2页。
[38]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39]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38-139页。
[40]谢本书:《龙云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142页。
[41]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39页。
[42]《何应钦为滇省退伍壮丁转作补充之用电》(1937年8月28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2页。
[43]《龙云建议所有精锐部队及重要武器宜分期使用电》(1937年9月4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2页。
[44]《蒋介石复电》(1937年9月6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3页。
[45]《蒋介石复电》(1937年9月6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3页。
[46]《蒋介石盼滇军速出发电》(1937年9月5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3页。
[47]《龙云呈滇军出师军费困难并请补助弹药电》(1937年9月6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5页。
[48]《龙云关于六十军出征并续派补充兵事电》(1937年10月9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10页。
[49]白肇学:《六十军鲁南抗战述略》,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90页。
[50]《卢汉报各方对滇军评价及沪战等情形电》(1937年11月7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15-16页。
[51]华企云:《满洲与蒙古》,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第1页。
[52]参见段金生:《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
[53]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铅印本,“自序”第5-6页。
[54]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铅印本,第5-7页。
[55]黄慕松:《我国边政问题》,南京:西北导报社,1936年,第40-43页。
[56]边事研究会:《发刊词》,《边事研究》创刊号,1934年,第3页。
[57]参见段金生:《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思想战线》2011年第1期。
[58]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59]张发奎此时与广西方面联合,逐渐形成新的西南政治问题,与北洋时代的西南军阀所指不同。参阅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2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60]戴季陶:《东北西北西南三个问题的总解决》,《新亚细亚》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61]社评:《应尽先注意西北建设》,《(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日。
[62]参见段金生:《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63]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87页。
[64]漆鲁鱼:《今年的“九一八”》,《新蜀报》1937年9月18日。
[65]《龙云11月16日复电》(1937年11月16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19-20页。
[66]《龙云恳坚持抗战既定国策贯彻始终电》(1937年12月23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第33页。
[67]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
[68]死灰:《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编:《云南杂志选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