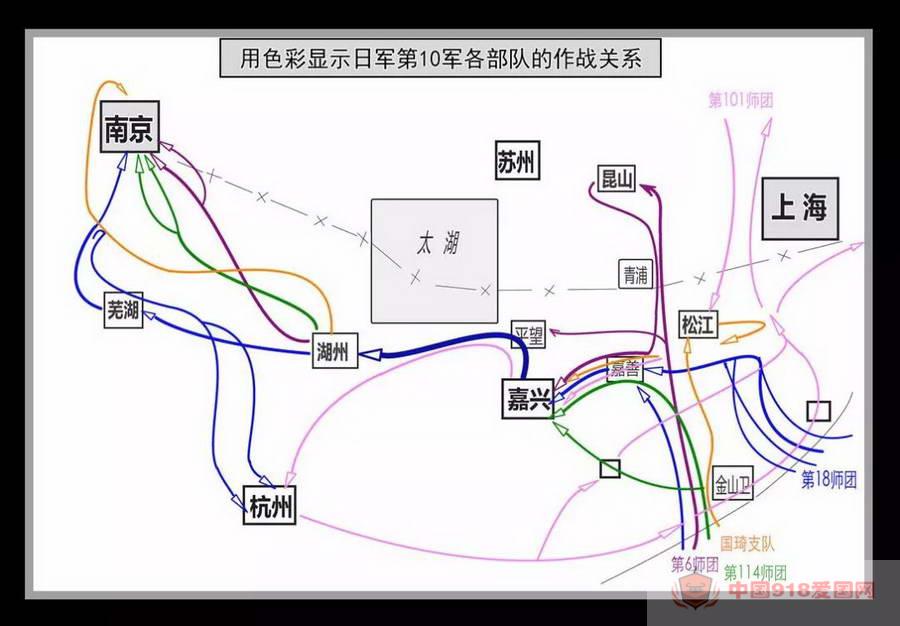摘 要:西安事变后上海等地出现的“统一救国运动”,表面由各界人士发起,实则为国民党一手炮制而成。国民党欲以“统一”的名义,通过“舆论的总动员”压倒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削弱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巩固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为此,国共两党及舆论界围绕是“联合抗日”还是“统一救国”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违背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和民主统一的历史大势,“统一救国运动”不仅在理论上遭受中共及有识之士的批驳,在实践上也昙花一现,最终以失败收场。“统一救国运动”的兴亡过程,预示着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才能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以往人们一般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历史事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不意味着国共两党从此一帆风顺地走向合作,其后还经历了诸多波折。为达到削弱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维护一党专政,包办将来抗战的目的,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曾在上海等地掀起了一个“统一救国运动”。该运动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大公报》称其“盛极一时”。[①]但其结果非如国民党所愿,反而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目前,史学界虽就抗日救亡运动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侧重于西安事变前中共、救国会和青年学生的活动,而对事变后国民党针对抗日救亡运动而策动的“统一救国运动”,以及该运动中国共两党、舆论界围绕是“联合抗日”还是“统一救国”而进行的交锋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对“统一救国运动”的前因后果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统一救国运动”的缘起
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国家统一不仅指一国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它还与国体(国家的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等诸问题相联接。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的统一必然和民主、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虽以“统一”相号召,欲凭借雄厚武力行独裁专制,但终不免违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落得个失败的下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虽继续以“革命党”自居,仍打着“反帝废约”的旗帜,但又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为全国之真实统一,即全国人民之思想必须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全国之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②]蒋介石在1931年7月《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一文中指出:“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③]即便在日本侵占东北,继而策动华北自治的民族危亡时刻,蒋介石仍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欲以“统一”之名打压各党派的反蒋运动和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这种不顾民族、人民利益的片面“统一”,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相背离,自然难以获得民众的响应。
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提出 “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④]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作为党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中共虽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后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逐步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无论过去有何政见分歧、利益差异和旧仇宿怨,均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觉悟,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携手共同救国。[⑤]中共的这一主张深受各界欢迎,推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以救国会等发起的救亡运动。蒋介石虽通过复兴社、诚社等组织在学生中培养亲国民党势力,以分化学生运动,并拘捕了沈钧儒等“七君子”,但依然无法控制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时人曾评价西安事变前北平的学生运动“受左倾势力的领导”,虽受当局的压迫,但其“表现的力量是十分重大的”,“右倾思想欲对抗而没有力量(因为没有群众)所以造成一面压倒的形势”。[⑥]而“七君子”事件更让国民党饱受社会舆论的批评,甚至连英国名流罗素、美国学界泰斗杜威等人也呼吁“释放逮捕的抗日志士”,表示“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自由”。[⑦]因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⑧]应该说,顺应了当时的主流民意。
但是,由于西安事变采取了扣留蒋介石的“兵谏”方式,且南京政府对西安和西北地区实行新闻封锁,歪曲对事变真相的报道,国统区的舆论多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12月25日,在蒋介石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条件后,张学良陪蒋飞赴洛阳,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许多城市民众张灯结彩,燃放爆竹以示庆祝。[⑨]蒋介石的声望以及民间对南京政府的认同倾向,较之事变前均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不过,蒋介石并不愿兑现其承诺,他在日记中所构思的新年大事包括“制服共党”“左倾思想之收服”“不造成内战而不放过内战,为对内统一之基本政策”等项。[⑩]为此,他拒放张学良回陕,并令中央军西进威胁西安,以逼迫杨虎城、于学忠等人接受南京政府关于东北军退驻甘肃、十七路军主力开回陕北,由中央军控制西安及其东西大道的善后方案,达到拆散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结成的“三位一体”之目的。同时,为配合蒋的行动,一场所谓“统一救国运动”也粉墨登场。
1937年1月16日,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刊登了一则重要新闻,宣称:近来本市各大学校长教授、中小学校长、教员著作家、新闻记者及工商各界人士,鉴于“陕甘善后,尚待中央筹划处置,而共党及失意政客,妄欲乘机利用封建残余势力,希图形成割据局面”,有违现阶段国家统一之需要,因而“发起统一救国运动,起草‘统一救国宣言’,广征签名”。该新闻附录了《统一救国宣言》全文,指出中国“反统一”的势力有三:封建的残余军阀;中国共产党以及所谓“人民阵线”或“联合战线”;为敌人做虎伥的汉奸等。并说中共所倡导的“人民阵线”目的在煽动人民反抗政府、以破坏国家秩序;“联合战线”就是要联合一切封建残余势力,阻害国家统一。提出中共如诚心救国,就应该取消“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宣言》最后号召“用整个民族的大力量,作全国舆论的总动员,于最短期间,纠正任何派别的歪曲意识,消灭任何地方的割据势力,不问是军阀,是汉奸,或是共党。我们深刻地相信,惟有巩固的统一,才是救国的基石。”[11]
该新闻宣称“统一救国运动”由上海各界人士发起,实则为国民党一手精心炮制。据1月17日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透露,《统一救国宣言》的具体起草者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2]这个名义上的“民众团体”,其实是国民党C.C.系的外围组织,由陈立夫任该会中央理事会理事长,潘公展任中央理事会秘书长,专门拉拢文教界的一些名流,为国民党摇旗呐喊。反共文人叶青便身列其中。叶青后来回忆道:当时潘公展和文化界十余人商讨如何反对共产党的人民阵线运动,因共产党的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他向潘公展建议:“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13]由此可见,国民党通过文化建设协会起草了《统一救国宣言》,并发起了“统一救国运动”。运动的目的旨在抹黑张学良、杨虎城为“封建的残余军阀”,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破坏国家统一的“人民阵线”,既配合南京政府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拆散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同盟,同时尽量削弱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让中共俯首听命于国民党的“统一”大业。
由于“统一救国运动”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对外又打着“民众团体”维护国家统一的幌子,让不明真相之人难免入彀,因而一时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内外人士的呼应。自1月中旬至3月初,来自湖北、河南、陕西、安徽、山东、江西等地国民党党部和商会、教育会、记者公会等团体的“响应电,不下百余通”。[14]上海、南昌、洛阳、厦门等地还成立了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标榜 “以拥护政府,统一政令、军权,完成除奸御侮,建设救国为宗旨”,吸引了不少社团代表参加,但其实权掌握在当地国民党市党部或文化建设协会的代表手中。[15]他们以所谓统一救国大同盟名义发表宣言和《呈三中全会文》,希望国民党中央责成国民政府“从速肃清为患后方之残余共匪,以杜可能之纷扰”,“从严处决以摧毁民族阵线为目的,而托名抗敌救国之反动分子”。[16]与此同时,文化建设协会等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纷纷撰写理论文章,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吹由国民党统一中国。上海市社会局令各校采用《统一救国宣言》,“颁发统一救国教学做实施大纲”。[17]上海市民众教育馆举办“统一救国运动宣传周”,宣讲“拥护领袖”、“坚定中心信仰”等观念。[18]甚至举行小学联合运动会,也有学生表演“统一救国徒手操”,“振发儿童民族精神”。[19]“统一救国运动”一时风生水起。国民党欲借此压倒中共和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它显然低估了中共的力量和舆论界的政治倾向。双方随之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二“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之争
由文化建设协会挑起的国共两党及舆论界的争论,涉及“统一”与“抗日”孰先孰后、中共是否是“反统一”的割据势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人民阵线”、统一与民主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其中心是“联合抗日”还是“统一救国”。
替国民党唱主角者依然是文化建设协会。文化建设协会在发起“统一救国运动”后不久,即由其所办刊物《文化建设》主编樊仲云“发信征稿”,于2月10日出版“统一救国问题”特辑,“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20]“统一救国问题”特辑共收录叶青、陶希圣、任一黎、郑学稼、潘公展等人撰写的十余篇文章,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统一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市民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是农民战争,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是“农民的军队和政府”,是反对统一的割据势力。[21]第二,中国若要救亡图存,需发扬“尊王攘夷”的精神,“尊王”指“统一于中央”,“攘夷”指“抗敌”,只有内部统一才能抵抗外敌,先安内而后攘外。统一可用和平方法,但不排除用武力戡乱讨逆。[22]第三,“联合”与“统一”不是一件事,联合的出发点是承认许多单位,永不消灭;统一则是将原有多个单位融化一个整体的单位。联合有承认割据势力之嫌,无异于把它看作构成中国的单位而予以合法的地位。实行联合,会因各势力利益不同难以团结对外。正确有效的办法是“统一抗日”,而非“联合抗日”。中共倡导“人民阵线”“联合战线”,主张联合各党派抗日,其“用意是在结合一切反政府的党派来反对政府,分裂国家”。[23]第四,国家统一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统一,以三民主义为共同信仰,拥护最高领袖。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中央政府应拥有强大的权力实行统一,而不能实行一般通行的民主政治。“只有统一完成,独裁方能退出政治的舞台”。[24]
除文化建设协会之外,亲国民党的刊物《读书青年》《时代动向》《新闻杂志》《中论》《会声月报》等也先后撰文,或诬蔑西安事变中红军“勾结”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反抗中央,“削弱抗战的力量”[25];张、杨的部队在蒋介石获释后,仍盘踞陕甘,破坏统一。[26]或混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的区别,说中共所主张的“人民阵线”不适合中国,将使中国陷入类似西班牙惨烈内战的局面。[27]或鼓吹“真正的统一,是必属于各种群团放弃与解散其个体单位的统一”,国民党“足以代替其他一切党派的力量”。[28]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还发表骆美奂的专文《所谓中国人民阵线的真相及其理论的检讨》,诋毁中共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藉抗日名义发动广泛的人民阵线”,利用救国会为外围组织反对现政府及国民党。并指责中共关于“联合阵线”中存在矛盾和斗争的说法,是自召内乱而非统一御侮。[29]
简而言之,国民党及其知识分子力图全面抹煞中共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意义,塑造中共煽动西安事变、破坏统一、不顾民族利益的负面形象,以便“降服”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使国民党集中“统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大权,巩固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上述谬论自然遭到中共及有识之士的严厉驳斥和批判。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从陕北采访归来的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阐明中共及红军并未参加西安事变,只是在事变4日后才派代表进入西安,他们力主和平,平息“二·二事件”东北军少壮派枪杀王以哲的风波,促进了事变善后问题的和平解决。该文指出,在中共的政治理论中,中国不需要反对法西斯的国内对立的人民阵线,而需要和平统一, “以统一的力量防御国家之生存”。中共的抗日主张不是外界所说的“人民阵线”所宣传的内容,而是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该文还透露,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蒋介石的方式不妥,但其动机是不满中央当局的“剿匪”政策,欲抗日“重返家园”,西北大多数军民并无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最多不过政策的商讨”。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当前的政治大问题“要有一番缜密的商讨”,给西北军民及全国民众“好消息”。[30]范长江的文章揭示了国民党统治区被掩盖的西安事变真相,展现了中共维护民族利益的良好形象,在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员、中共地下党员柳湜在《申报》连载《统一救国的真诠》一文,援引范长江的观点,斥责骆美奂将民族联合阵线与“人民阵线”混为一谈,无视中共倡导和平统一抵御外侮的事实。并指出:不同的政派及个人在统一过程中,对实际的救国行动难免有不同的意见,“一个策略一种战术总要通过各种讨论才能确定,并且一个正确的策略往往总是经过无数争辩才能得到”,恐惧而回避应有的斗争,“不能不是对联合战线有利而是对共同的神圣战争的一种不忠实”。[31]《民彝旬刊》、《文化动向》等杂志发文批判了上海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所谓肃清“为患后方之残余共匪”,处决“托名抗敌救国之反动分子”的谬论,认为其不顾民众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不请政府抗战救国,却热衷于打击主张抗日的共产党、救国会“七君子”以及“一切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获罪的民众和青年”,其结果将使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不能在抗敌的条件下团结起来,而滞留在党争、内战的混乱阶段,“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32]文章指出:中国不统一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以发动整个民族的对日抗战”,政府不抗战即不能博得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不能消除与共产党的歧异。拿统一做抗战的条件,事实上行不通,“由抗战以达到统一,才是中国目前统一运动的正轨”。[33]
上海《世界观》杂志开辟了“统一救国问题特辑”专栏,针对文化建设协会的“统一救国”论提出了三点不同意见。其一,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忽略民族危机下国内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要求共同抗日,以及国外英、美、苏等国希望中国加入和平战线,反对德、意、日侵略战线等因素。并非只有“市民阶层(资产阶级)”才能担负起统一的任务,工人和农民大众才是民族解放的基本力量。[34]其二,判断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否封建割据,要看那里是否有帝国主义的背景,领导者是不是封建军阀和地主,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是压制人民的,是不是反对国家统一的。“如果那里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割据的,是主张民主、解放民权的,是保护人民利益、改善人民生活的,是主张全国联合抗日,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就不能看作是军阀割据”。而苏维埃政权显然“是属于后者的”。[35]其三,大敌当前,“抗日第一”,提倡“尊王攘夷”、“不放弃以战争求统一”,违背了孙中山的以民治求和平统一的遗教。国民党应吸取过去军阀“武力统一”失败的教训,继承孙中山遗志中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来完成中华民国的彻底统一。[36]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则发表吴亮平的《斥叶青张涤非任一黎学稼诸托洛斯基派》一文,批判了叶青、任一黎等人提出的所谓实行“联合”,因各势力利益不同,难以团结对外;“只有统一完成,独裁方能退出政治的舞台”等观点,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各阶级在亡国危机下联合抗敌,联合之中虽因各阶级自身利害的不同,必然有矛盾和斗争,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与紧急的救亡任务之下,阶级矛盾变为次要,并可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适当的解决。联合抗日不是取消各阶级各党派间的矛盾,而是使各阶级各党派的个别利益,服从当前最重大的抗敌救亡的利益;换言之,民族利益也正是各阶级自己当前最大的利益,联合抗日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吴亮平认为,南京政府过去独裁的压迫政策,不仅催残民众的爱国运动,同时也使得南京与各省间、南京内部各派间的矛盾恶化,“使团结抗日受到了妨碍”。要适当地处理国内矛盾,非发展民主运动不可,只有国家行政机构的民主改革以及广大民众的民主运动,才能消灭封建割据的局面,以至逐渐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和解放。总之,“中国的真正统一,是与民主运动的发展不可分离的”。吴亮平文章强调:中共之所以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如改变苏维埃、红军名义等,正是为挽救中华民族所必须的,对国共双方来说,都有利益妥协。同时,中共绝不会取消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不会放弃对自己革命力量的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与政治领导之下,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37]
此外,由罗隆基任社长的《北平晨报》先后刊发《中国应如何实现统一》《“统一救国”之意义》《我们需要民主的统一》等多篇社论,力陈“武力统一之为用最不彻底,影响亦最恶劣”,主张“摒弃对内的武力”,“专用民力、政治力、内力、经济力”来谋求和平的统一,进而实现“民主的统一”。[38]社论认为,“统一救国”这一口号在字面上无可非议,但应“出之以民主的方式”,它应该促进全国的大团结,而不是为离间挑拨国内各党派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国内各党派之存在,当为民主国家之所容许,不能指为统一之障碍,且救国大业本非一党一派所得而包办,故各党各派之存在,更不得指为救国之障碍。”统一应该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为限,思想与言论不在其内,“不应成为钳制言论自由之凭藉”。[39]社论指出,过去的“武力统一”只是少数人的统一,欲将整个国家及人民置于“一二人或某一派系掌握支配之下”,牺牲了无数国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统一的意义,不能仅仅看“取消地域及阶层间的分裂或对立”,而不问统一的性质如何,是否值得国民一致的拥护。最好的统一是“民主的统一”,建立于广大人民的基础之上,国家的统治遵循宪治的轨道,“结果是民意代替了战争,使统一能实现;而法律代替了武力,使统一能维持”,全国一切实力、所有民众不但都能自由发展,而且都能得到良好保障。这种统一才是真正的,最能持久且最有价值的,值得全体国民的拥护。[40]
综上而言,中共及有识之士全面阐述了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政见不同的各党派团体,采取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及其知识分子诬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人民阵线”、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借西安事变破坏统一等谬论,揭露他们所鼓吹的“统一救国”的实质是以“安内第一”,欲让中共及各党派无条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包办将来的抗战。国民党及其知识分子的“统一救国”论,不但未获得舆论界的赞同,压倒当时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反引来一片责难之声,扩大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三 “统一救国运动”的消亡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既然“统一救国运动”在理论上饱受中共及有识之士的批评,无法站住脚跟,其在实践层面由盛而衰,以失败而收场,也是必然之事。运动初起时,国民党曾野心勃勃要征集“十万人签名”,甚至有党员提议成立中央、省、市、县、区各级“统一救国会”,以“使统一运动更能民众化、普遍化”。[41]但实际上,由文化建设协会起草的《统一救国宣言》只征得了近两万人署名,[42]北平文化界丁文浩、于成泽等412人联名表示“该项宣言之内容尚有待乎斟酌,不便冒然签名”。[43]上海文艺界虽也发表《对于统一救国运动宣言》,但只提到以文化势力消除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呼吁文化界不要分立成什么壁垒,“反乎时代与民族的需要”。[44]他们并不认同文化建设协会妄责中共是“反统一”势力的观点。尽管有的国民党地方党部通令各民众团体一律参加“统一救国大同盟”,[45]但该组织的存在仍只限于少数城市,远未达到全国各地“普遍化”的程度。“统一救国运动”虽在国民党统治区迷惑了一些群众参加,但其广度和深度远不及当时以学生和救国会为主体的抗日救亡运动。诚如中共中央4月5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言,“统一救国运动在国民党包办下,左派群众尚未能加入”,[46]它的群众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由于“统一救国运动”缺乏广泛的民意支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未采纳上海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提出的《呈三中全会文》关于“从速肃清为患后方之残余共匪”、从严处决“托名抗敌救国之反动分子”的主张,而表示对内取和平统一方针,并通过了“采取积极外交”“集中全国人才”“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等议案[47],以缓和“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民众迫切要求“停止内战”、民主抗日的呼声。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还不打算承认中共等持不同政见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而想方设法限制和削弱其力量。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坚持要求中共缩小红军改编后的军队编制、不设总指挥部、朱德和毛泽东离开军队、边区政府正官长由中央派遣等,并避谈中共起草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提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以达到取消中共独立性及对革命力量领导权的目的。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查禁《民彝旬刊》《世界观》等进步刊物,[48]罗织所谓救国会“容共”、反政府及推行人民阵线等“罪状”,对沈钧儒等“七君子”提起公诉,并指使国民党籍学生组织的北平新学联抵制中共领导的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时称“旧学联”),多次拒绝后者的“学运统一”主张。[49]在5月4日“五四运动扩大纪念会”上,北平新学联因不满旧学联对主席团人选的意见及演唱救亡歌曲,竟武力相向,殴打其学生代表。与会的国民党籍教授陶希圣、杨立奎等人也指责旧学联歌唱“保卫马德里”,就是挑拨中国分裂;并说:“真共产党投降了,假共产党还捣乱。”[50]国民党打着“和平统一”的旗号,行压制中共等其他党派力量和言行之实,这种“和平统一”虽不像“武力统一”那样硝烟四起,但其目的仍是实现一党专政,不过其手法具有蒙蔽性。
中共中央除在国共谈判中坚决维护党组织的独立性和对红军改编后的军队领导权之外,决定党目前工作的中心是“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以取得最后真正的和平与抗战的胜利,并打破少数野心家独裁专制的企图,“而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得以产生,并将他放在巩固的基础之上”。[51]为此,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释放沈钧儒等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彻底修改侵犯民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52]并呼吁国民政府修订1936年5月所颁布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废止对选民年龄、宣誓手续的限制,取消指定或圈定代表的钦定办法,增加各党派及学生会的代表名额等,以使国民大会真正民主化,“以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纲领与发动对日抗战”,实现抗日的民主统一。[53]由中共领导的北平旧学联一方面揭露陶希圣、杨立奎等利用新学联制造“五四事件”,破坏学运的阴谋;另一方面仍开诚布公地致信新学联,重申“国家民族的危机,需要我们统一的力量来挽救”,建议“集中所有原属贵会及本会的各合法学生会,择期召开代表大会,以最民主的方式决定学运统一诸问题”。[54]中共的这些主张获得了众多爱国人士的响应,各报刊纷纷发表有关国民大会和宪政的文章,“民主的呼声弥漫于全国”,有人兴奋地称之为“民主运动年”。[55]营救“七君子”的言论日渐高涨,并随着6月11日南京政府开庭审理沈钧儒等人,而掀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北平新学联原本是利用西安事变后部分学生对蒋介石的同情而成立起来的,此时竟面临“底下的群众极为动摇”,倒戈加入旧学联的窘境,连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陈公博也不禁感叹:“北平旧学联近加入者二千余人,声势似颇浩大。”[56]
虽然,国民党仍力图压制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如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共党近日对沈钧儒案等之宣传,及其对国民大会选举修正意见,仍以反对本党为唯一对象,毫无异于过去之行动……如其果欲诚意合作,应属其彻底改正,从速停止此项宣传。”[57]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也制订了所谓“一面充实新学联,一面设法消灭旧学联”的“统一学运组织之基本方法”[58],由新学联出面要求旧学联“以个人资格参加本会”[59],欲一举吞并对方。但这根本挡不住多数民众对抗日、民主、统一的心声,中共所倡导的民主运动一呼百应,难以阻遏,而国民党的“统一救国运动”反呈衰落之势。如果说5月初还有同情“统一救国运动”者建议:救国应有三到,即唤起民众(嘴到);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手到);剑及履及,收回失地(脚到),否则专务空谈,“统一救国的声浪,即便高唱入云,大炮一响,依旧手忙脚乱,无济于事”。[60]那么,到了6月初,征诸各大报纸的新闻报道,连这种怒其不争的谏言也难寻觅了。“统一救国运动”的消亡,使得国民党最初欲借“舆论的总动员”支持其一党专政的迷梦成为了泡影。国民党不得不在新修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中取消了对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候选人的圈定权,增加了选举的自由度等。北平新学联也被迫承认“根本没有对内斗争的必要”[61],同意与旧学联合并统一。7月4日,旧学联制定了一个彻底统一学运的方案,即由两团体各派代表若干人合组“北平学运统一促进委员会”,推动各校同学用民主方式选举新学生会,再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新会章,产生执委会。执委会成立之日,该委员会和原有两团体同时宣告解散,“统一后的学联不继承原有两团体之任何一系统,而为北平全体同学之总代表机关”。[62]可惜的是,3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学运统一进程被迫暂时中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和严峻的抗战形势,不再坚持将沈钧儒等人定罪并送至反省院,以及国共谈判红军改编问题上的苛刻条件。7月31日,“七君子”光荣出狱。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从而成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内统一与团结的局面”[63],为八年全面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国民党放弃过去的武力“剿共”政策,与中共携手抗日,值得肯定。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党仍未改变长期以来的统制政策,“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不可能实现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64]这不仅表现在国民党始终没有承认和公布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也体现于它并无诚心召开真正民主的国民大会。国民党虽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做了上述修改,但在条款中又限定该大会职责只是“制定宪法及决定宪法实施之日期”,且增加了政府指派代表240人、中央候补执监委员为当然代表等不合民主的条款。[65]即便如此,国民党仍于10月4日以“外患突发,御侮孔亟”等理由,下令延期举行国民大会。[66]直到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才登台亮相。当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自诩“始终以建设中国为独立自由、统一民主的国家为我平生的志事”之时,[67]殊不知几年后他败退台湾,中共领导人民建立了真正统一民主的新中国。
“统一救国运动”的兴亡过程,预示着国民党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作为执政党,国民党拥有较中共更充分的政治经济资源,却不能动员广大民众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如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所言:国民党若要在人民心目中提高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地位,那开放党禁,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是最好的办法。“那些一方面用一切方法压迫其他党派的群众运动,而另一方面想创造在国民党包办下的‘统一救国运动’,其结果是一定要失败的”。“民国二十六年的历史,不但证明武力统一中国的不可能,而且也证明独裁统一中国的不可能”。[68] 漠视人民民主的国民党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谁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不言自明。
注释
[①]《释统一救国》(社论),《大公报》(上海,下同)1937年3月24日,第1张第2版。
[②]《三次全代会重要议决案:党务政治外交军事》,《国闻周报》(上海,下同)第6卷第14期,1929年4月14日,第11页。
[③]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50页。
[④]《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⑤]《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21—522页。
[⑥]田光程:《最近学生界的严重问题——青年思想上的冲突、忧患与挽救》(1937年1月4—5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第343页。
[⑦]《英国名流罗素等营救章乃器等七人》、《美国学界泰斗杜威等营救救联七领袖电》,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料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16-317页。
[⑧]《张学良杨虎城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1936年1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2—380页。
[⑩]《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1日, “General19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抄件。
[11]《本市各界努力统一救国运动》,《申报》(上海,下同)1937年1月16日,第4张第13版;《本市各界发起统一救国运动》,《大公报》1937年1月16日,第2张第7版。
[12]《本市文化界发表统一救国意见》,《申报》1937年1月18日,第4张第13版。
[13]任卓宣(叶青):《我在上海反共之回忆》,帕米尔书店编辑部:《任卓宣评传续集》,台北:帕米尔书店,1975年,第13—14页。
[14]《全国响应统一救国》,《申报》1937年3月3日,第3张第10版。另参见《汉各团体发表通电》、《鄂各团体响应统一救国宣言》、《全市教育界宣言赞成统一救国运动》、《开封各团体来电响应统一救国运动宣言》、《鲁省党部响应统一救国运动》、《皖陕两省党部响应统一救国运动》、《京市商会电致沪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昨又接响应电》、《县党部通电响应统一救国》,《申报》1937年1月24日,第1张第3版;1月29日,第4张第15版;2月7日,第6张第23版;2月18日,第4张第13版;2月21日,第4张第14版;2月22日,第4张第13版;2月26日,第1张第4版;3月7日,第4张第14版;3月8日,第3张第9版。
[15]《本市组织上海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全国响应统一救国》、《六日中央社电》,《申报》1937年2月16日,第4张第14版;3月3日,第3张第10版;3月7日,第1张第3版;《七、江西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5—1018页。
[16]《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昨发重要宣言》,《申报》1937年2月17日,第4张第13版。
[17]《社会局令各校采用统一救国宣言》,《申报》1937年2月20日,第3张第12版。
[18]《市民教馆宣传统一救国运动本月份中心工作》、《市立民教馆主办之统一救国运动今晨揭幕》,《申报》1937年3月3日,第4张第16版;3月23日,第2张第8版。
[19]《小学联运今晨开幕》,《申报》1937年5月6日,第2张第8版。
[20]任卓宣(叶青):《我在上海反共之回忆》,《任卓宣评传续集》,第14页。
[21]叶青:《统一救国的途径》,《文化建设》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5—10页。
[22]潘公展:《统一与和平》,《文化建设》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156、160页。
[23]叶青:《统一救国的途径》、任一黎:《中国的统一问题》、陶希圣:《怎样实现统一》、潘公展:《统一与和平》,《文化建设》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17、22、51、158页。
[24]孟真:《国家统一与文化建设》、文夫:《统一与民主自由》、任一黎:《中国的统一问题》、学稼:《统一运动与中国斯太林党》、吴铁城:《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陈高傭:《统一救国应使国民意识统一》,《文化建设》第3卷第5期,1937年2月10日,第1—3、24、31、58—59、67页。
[25]《再论统一救国》,《读书青年》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20日,第1页。
[26]冷:《统一救国运动》,《时代动向旬刊》第1卷第4期,1937年2月1日,第3—4页。
[27]《所谓人民阵线》,《新闻杂志》第1卷第12期,1937年2月,第23页。
[28]梁客浔:《统一与联合》,《中论》第15期,1937年2月20日,第1—2页。
[29]骆美奂:《所谓中国人民阵线的真相及其理论的检讨》,《中央日报》1937年2月4日,第1张第3、4版。
[30]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大公报》1937年2月15日,第1张第3版。
[31]柳湜:《统一救国的真诠》,《申报》1937年2月20、21、23日,第11、10、9版。
[32]《进行中的统一救国运动》,《文化动向》第1卷第2号,1937年3月20日,第6页。
[33]秀明:《统一救国运动的批判》,《民彝旬刊》第1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第6—8页。
[34]胡黎人:《关于统一运动的基本认识》,《世界观》第1卷第1号,1937年4月1日,第4—6页。
[35]殷冷:《和潘公展先生讨论统一与和平》,《世界观》第1卷第1号,1937年4月1日,第12页。
[36]谢雨田:《中华民国统一运动史的检讨》、殷冷:《和潘公展先生讨论统一与和平》,《世界观》第1卷第1号,1937年4月1日,第9、12—13页。
[37]亮平:《斥叶青张涤非任一黎学稼诸托洛斯基派》,《解放》第1卷第3期,1937年5月11日,第9—14页。
[38]丝:《中国应如何实现统一》,《北平晨报》1937年2月23日,第2版。
[39]治:《“统一救国”之意义》,《北平晨报》1937年3月24日,第2版。
[40]应:《我们需要民主的统一》,《北平晨报》1937年3月25日,第2版。
[41]明公:《如何做统一救国运动》,《统一评论》第55期,1937年3月27日,第3—5页。
[42]《署名统一救国宣言近两万人》,《申报》1937年2月7日,第5张第18版。
[43]《关于统一救国运动》,《益世报》(天津)1937年4月12日,第1张第3版。
[44]《洪深傅东华等召集文艺家座谈会》,《申报》1937年1月30日,第4张第14版。
[45]《市党部通令参加统一救国大同盟》,《进化》第2期,1937年3月15日,第18页。
[46]《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452页。
[47]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29、445、447页。
[48]《“七七”事变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的报刊目录》,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71—172页。
[49]《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再度呼吁学运统一宣言》(1937年2月28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1937年4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68、287页。
[50]于秀:《今年北平的五四事件》,《光明》第3卷第1期,1937年6月10日;中大荣:《记北平新学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0—152页。
[51]《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1937年4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2、201页。
[5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1937年4月12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90页。
[53]《中央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1937年4月11日)、《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1937年5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85、206页。
[54]《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致学生联合会的公开信》(1937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第297—298页。
[55]澄平:《民主精神与青年运动》,《青年中国》第1卷第15期,1937年6月,第6页。
[56]张谨斋:《关于半年来北平学生工作报告》(1937年7月17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3册,第538页;《国民党中训部签密函》(1937年5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第423页。
[57]《致顾祝同电》(1937年5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一般资料》,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278-008。
[58]《国民党中训部拟订“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文件》(1937年5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二九运动》,第425页。
[59]《平市学生联合会为统一学运发表谈话》,《学生周报》第8期,1937年5月27日,第3版。
[60]卖愁:《三到》,《申报》1937年5月5日,第5张第19版。
[61]《新学生团体发表谈话》,《北平新报》1937年6月23日,第4版。
[62]《北平学生团体昨开执委会议》,《北平新报》1937年7月5日,第9版。
[63]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85页。
[64]《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6—370页
[65]《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选举法》,《司法公报》第189号,1937年6月2日,第1—10页。
[66]《国民大会决定延期举行》,《申报》1937年10月5日,第4版。
[67]《主席勖勉代表完成制宪任务》,《申报》1946年11月16日,第1张第1版。
[68]洛甫:《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1937年4月11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