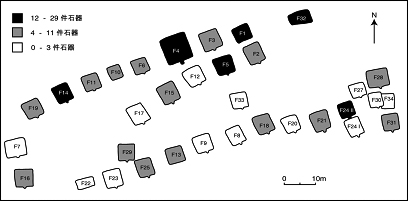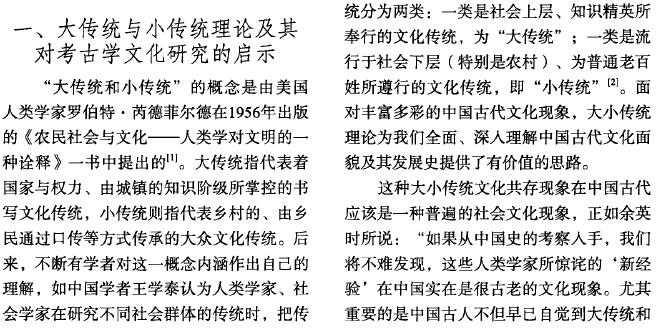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受中国玉器全集编委会委托,在辽宁省同行及朋友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北出山海关,从沈阳西到建平、东达旅大,对辽宁省境内以发掘品为主体的史前古玉考古学标本,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参观学习。首先是半岛地区和沈阳新乐出土的斧、锛、凿等玉质工具上,分别保留着麻点状锤击及剥片法成坯等治石技法痕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时还有幸在牛河梁工作站住下来仔细观摩红山文化玉器。无论箍形器内外壁保留着抛物线型弧曲线的残迹、兽形�豁口部位的线切割弧线,还是以不对称无规则打洼形成边刃状透雕或沟槽为特征的勾云形�,无一不在其极具鲜明个性的同时,在琢玉工艺的发展阶段上仍然保持共同性。说明在红山玉器上,确已形成有别于治石技法的琢玉工艺。连同长江下游地区史前古玉考古标本的多年观察揣摩,构成了编辑玉器全集第一卷的基本框架。
随着第一卷资料的汇集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几次境外访问,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比考古标本复杂得多的传世玉器。众所周知,任何古代遗物在考古学家发现之前,都有可能被人们发现,并以各种形式保留下来或重新湮没。许多重大的考古标本,并不都是由考古学家最先发现或研究。安阳的商代甲骨,不就是当作药材来出售吗?怎样从传世古物的甄别中补充、扩大研究成果或有所启发,乃是考古学诸子份内之事,也是各家学术素质的一种反映。良渚玉器上的铭刻符号,就是最先发现在传世品上。当古器物具有商品价值以后,历代仿制品不断涌现,极大地增加了传世古物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自然不能在传世古玉商业效应看好的今天,可以和各种鉴赏家、收藏家那样选择它们的“价值”。假如古玉的鉴赏真的以玉材的天然质地的美感和雕琢工艺的技巧为着眼点,自然不存在着各器的琢雕年代及仿伪问题。严格地应该说,任何仿制品都是仿制时琢玉工艺的真实标本。所以在古玩坊肆或某一收藏单位的传世古玉中,出现若干件以金属砣具为工具仿琢的良渚玉器,是很常见的事。如果以此为凭据论证史前时期的良渚文化已经出现砣机或原始砣,则显然是自欺欺人之说。目前已知最早仿制的良渚玉琮,至少可以远在十八世纪的乾隆年间。早在卢芹斋出版物中收录红山型箍形器之前,就有仿琢的良渚玉琮流传到海外。决不因为当时考古界还完全不知道红山玉器和良渚玉器的真实年代而成为排除各该玉雕件仿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随着以考古标本上判读到各该时期的琢玉工艺痕迹为依据,并从工和艺的深层轨迹上去探索琢玉工艺的发展阶段,这一当代古玉考古学研究命题的进展,也将为鉴别传世古玉找出一条可靠的新途径。
几天前又有机会重访沈阳,在郭大顺、孙守道二位学长的亲切接待中,再一次学习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史前玉器,看到了阜新查海发掘的前红山文化玉器、早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发掘的红山型(系)玉器、近年红山新发掘所得尚未正式发表的玉器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实物。也重新观察了一些以前学习过的标本,以期温故而知新。如同北国隆冬带给这群南方来客的新鲜感一样,这次学习留下了深刻印象,札记如下。
一、查海出土的所有玉�,其豁口部位都十分清晰地保留着近似同心抛物线型的弧线痕迹。此种痕迹也出现在南方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所有玉�的相同部位。这种以高硬度的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为特征的琢玉工艺,不仅可以将辽东半岛及新乐的玉质工具上保留着的治石工艺痕迹区分开来,而且消耗时间、精力及难度都比治石工艺高得多。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史前时期任何以实用为目的石制品上见到这种痕迹。可见中国古代石、玉制造工艺分野的年代,当在距今七、八千年之间。史前时期的玉器并不是使用治石工具和工艺来制造的,同时也说明古人要寻找硬度超过6.5到7度这样高硬度材料,并将它制造成需要的物品,决不象人们想象或用文字描写那样轻松容易。特别需要指出,这种琢玉工艺痕迹绝不是象砣机独有的那种等径圆弧。可以证明当时带动解玉砂的琢玉工具,并不是象砣机那样的圆盘形的旋转体。比较查海玉�和红山兽形�豁口所出现的同类痕迹,后者比前者规整得多,反映出此种琢玉工艺长达数千年跨度的前进脚步。不难想象,从出现琢玉工艺到发明砣机,可能还要长得多的岁月。
二、查海匕形玉片启示了红山玉器上经常见到的不对称打洼工艺的源头。六件匕形玉片长短不一而厚薄相若,凸弧面中脊部位都能观察到一道大致平直狭长的平面,保留着坯件原貌。每件凹洼槽的两侧均不对称,每侧坡面的弧曲度也不一致。有些凹洼的底端,还可以观察到纤细的纵向线条,应属于手工打洼工艺之痕迹,这种凹向洼槽的截面,虽然有时会在底端形成一道中折线,称之为“V”字形剖面恐怕还是名之为凹槽或洼面更贴切。这六件玉匕上的凹洼不属旋转性圆轮――砣机的制品,大概不会引起分歧或异议。
三、勾云形�是红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玉器之一。在勾云形玉�上见到的打洼工艺,显然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已经很难见到查海玉匕那样简单的纵向凹槽,勾云形�的打洼工艺可分为洼面不涉及器缘的全洼型和洼口宽端冲向器缘的半洼型两种。全洼型的平面形态几乎全部表现成弧曲线,如能仔细观察半洼型两侧坡面的尾端――即尖细浅的一端,也都呈现一定程度的弯曲坡。全洼型的洼槽坡较缓和,底端通常不见折角,而其凹洼的中段往往穿透器壁形成刃边状的透雕效果。这一性状时常使研究者误解为打洼工艺之目的,甚至费尽心机地想象推测某种原始砣具的存在。只要稍稍认真地观察全洼型穿透器壁部位的两个端点,就能发现其一端是一圆形钻孔,另一端的正背两面则表现为与透雕走向的延长线相一致的“V”字形洼坡,这道洼坡在正、背两面表现为和谐的对称性。这种以钻孔和线切割组成的透雕镂空工艺,不仅时常在良渚文化玉器上见到,也可以在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地及安徽含山凌家滩两地用作连接玉璜中段两端点的穿缀工艺中见到的常用技巧。所以在红山文化的勾云形佩上出现这项工艺,透雕镂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勾云形�上的全洼型打洼工艺只是在透雕的基础上,将其两侧修磨成边刃状弧坡,这就成为红山文化有异于其他史前琢玉的特征。在这样两道洼面之间,不时会出现棱状折线。由于相邻的两侧洼坡各自呈现无规则不对称的特性,致使这些棱线也具有无规则不对称的粗犷特征。如果说红山玉器发掘所得的每一件勾云形�都充分地表现了这种工艺的典范,成为体现雕件形态最传神的表现手法。那么,相信每一位有上手机会观察红山勾云形�发掘标本的研究者,都会发现凹槽坡的弧曲度,都会呈现无规则不对称的特征。这一工艺的起源,除了功能性需求之外,起初可能只是因势利导地局部修治当时玉料剖割工艺无法避免的坯料起伏面。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成器表的装饰工艺。
在金属工具出现之前,有没有以旋转性圆盘为体征的原始砣,是当前史前琢玉工艺研究的敏感问题,更是唯砣方能琢玉这一传统观念中要害性的头等大事。有人自称依据红山、良渚等史前古玉外表,“创造性”的设想出中间较厚,边缘呈钝刀或轮边状的两种圆砣,似可认作“唯砣方能琢玉”论的代表性论证。一般地说,琢玉工艺和古今任何一项创造技术一样,无不受到材料和工时两方面功利效益的制约。如果将琢玉工艺分解成剖料成坯、琢磨成器两个阶段。以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工艺,主要用于开料阶段,这表明在人心目中玉料的珍贵远远超过工时消耗的价值,为了节省珍贵的玉料不惜消耗比打击技法等治石工艺多无数倍的劳动量。在修坯成器阶段,加工的部位仅仅局限于外表,此项修磨工序没有必要一定采用以大量耗时为代价的间接摩擦,完全可以采用伴随磨制石器出现的直接摩擦――即治石技艺。任何驱动解玉砂的手段,都可以驾轻就熟地达到目的。比较前后两段工序,剖料成坯在以光素器表为主的史前玉器时期显然是琢玉工艺的主要方面或主攻方向,具有本质性的意义。这就是史前玉器和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以器表装饰为主体的琢玉工艺的重要区别点。因此,在史前时期剖料成坯工艺更多地吸引着治玉者的关心和注意。而增加砣具的厚度,哪怕只增加砣具中心的厚度,既不能省工,也无法节材。如若用这种“原始砣”去剖料成坯,不但要比线切割或片切割花费更多的工时,可能被磨耗的玉材要比打击成坯还要多。当然,先进的工具或工艺不一定首先出现在最重要工序,更不能排除史前时期的某种工艺产生,超越后代功利法则的多种可能性。或许在史前人们的原始观念中,对太阳或某种类似圆盘被赋予神圣的魅力。巫术或其他多种偶然因素都可能成为出现砣具的最初动机。但是可能性不等于事实,只有当时确有这项工艺存在,并且在制品中找到确切的证据,才能确认认这项工艺的存在。如何判读旋转性圆盘留下的痕迹,单凭中间宽深、两端尖浅八个字,无论如何不能界定砣具特有的文字表述。许多工具或工艺都会留下和这八个字相彷佛的痕迹。除了大家都熟悉的等径圆弧、圆心角小于180度、作用力表现为向弧性等圆砣琢玉的特异性指征外,由于圆砣为硬性物体,运动时不可能任意改变自身的形状。所以用圆砣雕琢的线段或沟槽,其截面的两侧或一侧势必形成相似的斜面。不妨大胆假设,红山时期已经拥有剖面各异的多种砣具,而且每一砣具的使用寿命都很短,因而同器的每一道洼槽都要采用许多个不同剖面不同直径的圆砣,甚至每一道沟槽就使用几个不同的砣具,那么至少在每一砣具有效直径范围以内的同侧剖面上,总应该出现或保留相应对称的坡面。但是,据我见到红山玉器的考古标本,却找不到这类与旋转性圆盘相吻合的痕迹。大家都知道金属砣具在弯转部位多有岐出。砣具确实是琢玉的先进工具,尽管解玉砂的硬度高于玉,旋转着的圆砣又带给解玉砂一定的作用力,但是玉材毕竟也是高硬度物质,任何稍有琢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仅仅因器表修磨时用力不均,就会使器表留下两道如此深凹的弧痕?!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类器表凹窝都产生于器表修磨之前。其作用力的方向均不垂直于器面而与器面平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些属开料成坯时切割面所呈现的波浪形起伏,在器表修整时磨去了凸突部位后就剩下了这些凹窝。所以这种凹窝的深度实际上已经减少了不少。以前我曾写过“在良渚文化玉器上,至今没有见到砣具琢玉的痕迹”,在这次学习中所见到红山玉器的考古标本上,仍然没有见到砣具的踪影。
四、两件兽面纹“丫”字形器。两器均为文物店征集品,同类器目前还没有见到发掘标本。一白一青,白者扁薄而青者浑厚,二者外形相近而神态有别。前者以浅钻孔表现鼻孔与嘴角,体形正反两面不对称。无论表现眼睑、嘴裂等额部阴线及通体近似平行凹弧线,每一线条之深浅粗细均不一致,仍然保持不对称,无规则的古璞特征。后者体形略呈椭圆形,整器前后、上下及左右两侧大体均衡,头部纹样不够清晰,仅隐约可辨,通体环绕着和谐的平行凹凸纹。整体雕琢水平均较前器进步得多。推测两者的雕琢年代亦有不短的差距。
五、两件玉鸟也是文物店的征集品。以青白玉雕琢的一件,平面略近方形。玉料颇佳,总体形态及两翅都保持对称布局,颈部有一道横向凹沟,槽壁陡直底缘平齐宽深若一,截面呈U字形,应属砣具雕琢产物。特别值得注意两侧的对称部位,各有一道纤细挺直的纵向阳纹,更是前所未见之杰作。玉鸟是红山文化发掘品中常见的器种,但在已见到的发掘标本中还没有雕琢工艺如此精良的标本,不能不使人疑虑此鸟的雕琢年代。
六、箍形器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种。虽然外形简单,通体光素没有任何装饰线条,但要掏空内壁形成穿透的大孔腔,在当时决非易事。就剖料成坯工艺而言,它是红山玉器发掘品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如果从单体玉制品的玉料利用系数的角度考察,其利用率是发掘所见红山玉器中最低的一种。但是掏割下来的孔芯仍然可以再次雕琢,从中透露出在总体设计上一材多器共用的高水平琢玉工艺的信息。这也是发掘所得红山玉器所仅见。
这次见到的几件箍形器都保留着一些土锈,但内外壁都没有保留切割的弧线。有幸能亲手揣摩其内外壁之间起伏弧曲度及其走向的变化,还是获得一些新的感受。起初此器之描述往往将横向断面称作椭圆形,以后改作扁圆形似较以前准确。一般说来,古玉的仿制者不一定能见到被仿制的原件,图片及有关文字描述自然成为仿制时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仿琢件是反映仿琢年代对该器认识或研究水平的物化表现。按照这次学习所得的体验,箍形器之体征,除器壁内外不均衡起伏之外,整体形态近似圆角梯形。即自下而上的每一水平横截面,近似不断增大的圆角梯形,不知是否比椭圆形或扁圆形更贴近实际。在近年所见之仿琢器,几乎毫无例外地忠实于椭圆或扁圆的造型。或许在不久之后,很快就有不同截面的箍形器应市,当今如要认真地识别一件传世玉器,除了鉴别者对相应考古标本的研究层次超过仿制者,似乎别无良法。
七、黑龙江省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是五十年代李文信先生的发掘成果,所得各件玉器的形状、用料及雕琢风格均近红山玉器。估计该墓地的绝对年代可能晚于红山文化。虽然不能排除出土玉器来自外地的可能性,但在空间坐标上,它们确实落在红山文化分布范围之外,不知是否暂时可称之为红山型(系)玉器。
在沈阳机场临别前,大顺以最新出版的《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相赠,甚喜。这一墓地的绝对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之际,报告书公布了发掘品中包含箍形器(M833:2),勾云形�(M821:5,报告称镂花坠),勾形器(M308:1,报告称雕花坠),臂饰(M659:7),璧(M853:13,报告称璧形坠)和玉�等红山型(系)玉器的线图和黑白照片。其中玉�即多达10件,从照片看豁口似有线切割的痕迹。报告称筒形器“截面为椭圆形”,“筒内侧有摩擦加工痕”,还在线图标出臂饰内臂的弧形雕琢痕迹。这些发掘标本虽然没有见到实物,但能说明以往在殷墟妇好墓及三门峡、侯马周代墓地出土红山型(系)玉器并非偶然,一概将它们当作早期遗留物品处置,看来未必完全妥当。八十年代初,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是我国史前玉器考古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前进,将红山型(系)玉器放到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作深层次的动态考察,应是深入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例如号称天下第一的玉勾龙,在已知诸器中不少是传世品,其中也有仿制品,有确切出土地点的仅有一例,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同类的考古发掘标本。三星他拉出土的标本,整体造型单调,器表也无复杂的装饰花纹,但又显露出秀丽雅洁的神态。有人称之为“雕工精湛,是红山文化中玉雕水准最高的一件”,评价之高似属绝无仅有。此器平面的空间范围,超过540平方厘米,获得并切割如此大面积玉料,而且整体厚薄平直匀称若一,确非易事。直径26厘米的大型玉璧在良渚玉器中已属不可多见之极品。红山玉器中最大的勾云形�长度只有22.5厘米。不论良渚璧还是红山�,玉料两面难免都存在不同的起伏高差。特别需要指出,玉勾龙的玉料利用系数不足原玉料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前面讨论过的箍形器。剩余的玉料固然可以雕琢他件,但箍形器芯还是一块完整玉料,而此类勾龙之剩料至少被分割成三小块,即便在今天,如若事前没有精心筹划一料多用的设计方案,并且掌握得心应手的开料工艺,也不可能如此大胆放肆地处理这样大型的玉料,何况视玉料为神物的史前古人。总观全国史前玉器的考古标本,玉料利用系数如此低小的制品别无他见。也就是说,象勾龙这样以玉材高消费理念设计的开料成坯工艺,在目前已知的史前考古标本中还没有见到过。
此次东北行之前,偶然获得上手观摩一件“天下第一”的机会,虽然不是三星他拉那一件,也可称三生有幸了。此器整体平直匀称,通体各截面弧曲度相若,鬣毛与龙体交接部位呈反向折角,交接部位走向明快和谐,比红山兽形�双耳背后之折角进步得多。鬣毛整体平直,外缘斜杀如刃边,近似红山风格,但两侧弧坡基本保持对称与红山有别。嘴裂、眼缘及顶额部位的网格纹,均用阴线刻表现,嘴、眼之阴线均一端宽深一端尖浅,但阴线两侧呈大致对称的斜段坡,故截面呈“V”字形。只在弯曲部位的坡面呈浅弧形凹曲,近似红山发掘品上打洼工艺。顶额部之网格纹,截面均呈“V”字形。此器之细部若与三星他拉那件标本的照片相比,此器缺少鬣背及斜刃部二处阴刻细线。红山文化的琢玉工艺也有优劣之分,已知的玉勾龙不一定琢于同一年代。仅观一器自然未能涵盖其余各器。但在没有获得确切的考古发掘品证实之前,不将此种器类的时空框架过早地锁定在红山文化之内,不一定不是科学的态度。如将未被正规的考古发掘所验证的传世玉器用作历史研究时,慎重对待,不能不是公正的做法。
我不曾参加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发掘的野外实践,也没有对东北地区史前诸文化有过系统的研究,对于传世玉器更不曾入门。一二次实地学习虽有得益,也只能获得一鳞半爪的知识。管中窥豹在所难免,班门弄斧抑或隔靴搔痒,或两者兼而有之,均属可能。姑记之,用以备忘,日后或有抛砖之效。
(责任编辑:高丹)
随着第一卷资料的汇集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几次境外访问,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比考古标本复杂得多的传世玉器。众所周知,任何古代遗物在考古学家发现之前,都有可能被人们发现,并以各种形式保留下来或重新湮没。许多重大的考古标本,并不都是由考古学家最先发现或研究。安阳的商代甲骨,不就是当作药材来出售吗?怎样从传世古物的甄别中补充、扩大研究成果或有所启发,乃是考古学诸子份内之事,也是各家学术素质的一种反映。良渚玉器上的铭刻符号,就是最先发现在传世品上。当古器物具有商品价值以后,历代仿制品不断涌现,极大地增加了传世古物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自然不能在传世古玉商业效应看好的今天,可以和各种鉴赏家、收藏家那样选择它们的“价值”。假如古玉的鉴赏真的以玉材的天然质地的美感和雕琢工艺的技巧为着眼点,自然不存在着各器的琢雕年代及仿伪问题。严格地应该说,任何仿制品都是仿制时琢玉工艺的真实标本。所以在古玩坊肆或某一收藏单位的传世古玉中,出现若干件以金属砣具为工具仿琢的良渚玉器,是很常见的事。如果以此为凭据论证史前时期的良渚文化已经出现砣机或原始砣,则显然是自欺欺人之说。目前已知最早仿制的良渚玉琮,至少可以远在十八世纪的乾隆年间。早在卢芹斋出版物中收录红山型箍形器之前,就有仿琢的良渚玉琮流传到海外。决不因为当时考古界还完全不知道红山玉器和良渚玉器的真实年代而成为排除各该玉雕件仿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随着以考古标本上判读到各该时期的琢玉工艺痕迹为依据,并从工和艺的深层轨迹上去探索琢玉工艺的发展阶段,这一当代古玉考古学研究命题的进展,也将为鉴别传世古玉找出一条可靠的新途径。
几天前又有机会重访沈阳,在郭大顺、孙守道二位学长的亲切接待中,再一次学习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史前玉器,看到了阜新查海发掘的前红山文化玉器、早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发掘的红山型(系)玉器、近年红山新发掘所得尚未正式发表的玉器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实物。也重新观察了一些以前学习过的标本,以期温故而知新。如同北国隆冬带给这群南方来客的新鲜感一样,这次学习留下了深刻印象,札记如下。
一、查海出土的所有玉�,其豁口部位都十分清晰地保留着近似同心抛物线型的弧线痕迹。此种痕迹也出现在南方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所有玉�的相同部位。这种以高硬度的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为特征的琢玉工艺,不仅可以将辽东半岛及新乐的玉质工具上保留着的治石工艺痕迹区分开来,而且消耗时间、精力及难度都比治石工艺高得多。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史前时期任何以实用为目的石制品上见到这种痕迹。可见中国古代石、玉制造工艺分野的年代,当在距今七、八千年之间。史前时期的玉器并不是使用治石工具和工艺来制造的,同时也说明古人要寻找硬度超过6.5到7度这样高硬度材料,并将它制造成需要的物品,决不象人们想象或用文字描写那样轻松容易。特别需要指出,这种琢玉工艺痕迹绝不是象砣机独有的那种等径圆弧。可以证明当时带动解玉砂的琢玉工具,并不是象砣机那样的圆盘形的旋转体。比较查海玉�和红山兽形�豁口所出现的同类痕迹,后者比前者规整得多,反映出此种琢玉工艺长达数千年跨度的前进脚步。不难想象,从出现琢玉工艺到发明砣机,可能还要长得多的岁月。
二、查海匕形玉片启示了红山玉器上经常见到的不对称打洼工艺的源头。六件匕形玉片长短不一而厚薄相若,凸弧面中脊部位都能观察到一道大致平直狭长的平面,保留着坯件原貌。每件凹洼槽的两侧均不对称,每侧坡面的弧曲度也不一致。有些凹洼的底端,还可以观察到纤细的纵向线条,应属于手工打洼工艺之痕迹,这种凹向洼槽的截面,虽然有时会在底端形成一道中折线,称之为“V”字形剖面恐怕还是名之为凹槽或洼面更贴切。这六件玉匕上的凹洼不属旋转性圆轮――砣机的制品,大概不会引起分歧或异议。
三、勾云形�是红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玉器之一。在勾云形玉�上见到的打洼工艺,显然有了长足的发展。首先已经很难见到查海玉匕那样简单的纵向凹槽,勾云形�的打洼工艺可分为洼面不涉及器缘的全洼型和洼口宽端冲向器缘的半洼型两种。全洼型的平面形态几乎全部表现成弧曲线,如能仔细观察半洼型两侧坡面的尾端――即尖细浅的一端,也都呈现一定程度的弯曲坡。全洼型的洼槽坡较缓和,底端通常不见折角,而其凹洼的中段往往穿透器壁形成刃边状的透雕效果。这一性状时常使研究者误解为打洼工艺之目的,甚至费尽心机地想象推测某种原始砣具的存在。只要稍稍认真地观察全洼型穿透器壁部位的两个端点,就能发现其一端是一圆形钻孔,另一端的正背两面则表现为与透雕走向的延长线相一致的“V”字形洼坡,这道洼坡在正、背两面表现为和谐的对称性。这种以钻孔和线切割组成的透雕镂空工艺,不仅时常在良渚文化玉器上见到,也可以在南京北阴阳营下层墓地及安徽含山凌家滩两地用作连接玉璜中段两端点的穿缀工艺中见到的常用技巧。所以在红山文化的勾云形佩上出现这项工艺,透雕镂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勾云形�上的全洼型打洼工艺只是在透雕的基础上,将其两侧修磨成边刃状弧坡,这就成为红山文化有异于其他史前琢玉的特征。在这样两道洼面之间,不时会出现棱状折线。由于相邻的两侧洼坡各自呈现无规则不对称的特性,致使这些棱线也具有无规则不对称的粗犷特征。如果说红山玉器发掘所得的每一件勾云形�都充分地表现了这种工艺的典范,成为体现雕件形态最传神的表现手法。那么,相信每一位有上手机会观察红山勾云形�发掘标本的研究者,都会发现凹槽坡的弧曲度,都会呈现无规则不对称的特征。这一工艺的起源,除了功能性需求之外,起初可能只是因势利导地局部修治当时玉料剖割工艺无法避免的坯料起伏面。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成器表的装饰工艺。
在金属工具出现之前,有没有以旋转性圆盘为体征的原始砣,是当前史前琢玉工艺研究的敏感问题,更是唯砣方能琢玉这一传统观念中要害性的头等大事。有人自称依据红山、良渚等史前古玉外表,“创造性”的设想出中间较厚,边缘呈钝刀或轮边状的两种圆砣,似可认作“唯砣方能琢玉”论的代表性论证。一般地说,琢玉工艺和古今任何一项创造技术一样,无不受到材料和工时两方面功利效益的制约。如果将琢玉工艺分解成剖料成坯、琢磨成器两个阶段。以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工艺,主要用于开料阶段,这表明在人心目中玉料的珍贵远远超过工时消耗的价值,为了节省珍贵的玉料不惜消耗比打击技法等治石工艺多无数倍的劳动量。在修坯成器阶段,加工的部位仅仅局限于外表,此项修磨工序没有必要一定采用以大量耗时为代价的间接摩擦,完全可以采用伴随磨制石器出现的直接摩擦――即治石技艺。任何驱动解玉砂的手段,都可以驾轻就熟地达到目的。比较前后两段工序,剖料成坯在以光素器表为主的史前玉器时期显然是琢玉工艺的主要方面或主攻方向,具有本质性的意义。这就是史前玉器和进入历史时期以后以器表装饰为主体的琢玉工艺的重要区别点。因此,在史前时期剖料成坯工艺更多地吸引着治玉者的关心和注意。而增加砣具的厚度,哪怕只增加砣具中心的厚度,既不能省工,也无法节材。如若用这种“原始砣”去剖料成坯,不但要比线切割或片切割花费更多的工时,可能被磨耗的玉材要比打击成坯还要多。当然,先进的工具或工艺不一定首先出现在最重要工序,更不能排除史前时期的某种工艺产生,超越后代功利法则的多种可能性。或许在史前人们的原始观念中,对太阳或某种类似圆盘被赋予神圣的魅力。巫术或其他多种偶然因素都可能成为出现砣具的最初动机。但是可能性不等于事实,只有当时确有这项工艺存在,并且在制品中找到确切的证据,才能确认认这项工艺的存在。如何判读旋转性圆盘留下的痕迹,单凭中间宽深、两端尖浅八个字,无论如何不能界定砣具特有的文字表述。许多工具或工艺都会留下和这八个字相彷佛的痕迹。除了大家都熟悉的等径圆弧、圆心角小于180度、作用力表现为向弧性等圆砣琢玉的特异性指征外,由于圆砣为硬性物体,运动时不可能任意改变自身的形状。所以用圆砣雕琢的线段或沟槽,其截面的两侧或一侧势必形成相似的斜面。不妨大胆假设,红山时期已经拥有剖面各异的多种砣具,而且每一砣具的使用寿命都很短,因而同器的每一道洼槽都要采用许多个不同剖面不同直径的圆砣,甚至每一道沟槽就使用几个不同的砣具,那么至少在每一砣具有效直径范围以内的同侧剖面上,总应该出现或保留相应对称的坡面。但是,据我见到红山玉器的考古标本,却找不到这类与旋转性圆盘相吻合的痕迹。大家都知道金属砣具在弯转部位多有岐出。砣具确实是琢玉的先进工具,尽管解玉砂的硬度高于玉,旋转着的圆砣又带给解玉砂一定的作用力,但是玉材毕竟也是高硬度物质,任何稍有琢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仅仅因器表修磨时用力不均,就会使器表留下两道如此深凹的弧痕?!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类器表凹窝都产生于器表修磨之前。其作用力的方向均不垂直于器面而与器面平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些属开料成坯时切割面所呈现的波浪形起伏,在器表修整时磨去了凸突部位后就剩下了这些凹窝。所以这种凹窝的深度实际上已经减少了不少。以前我曾写过“在良渚文化玉器上,至今没有见到砣具琢玉的痕迹”,在这次学习中所见到红山玉器的考古标本上,仍然没有见到砣具的踪影。
四、两件兽面纹“丫”字形器。两器均为文物店征集品,同类器目前还没有见到发掘标本。一白一青,白者扁薄而青者浑厚,二者外形相近而神态有别。前者以浅钻孔表现鼻孔与嘴角,体形正反两面不对称。无论表现眼睑、嘴裂等额部阴线及通体近似平行凹弧线,每一线条之深浅粗细均不一致,仍然保持不对称,无规则的古璞特征。后者体形略呈椭圆形,整器前后、上下及左右两侧大体均衡,头部纹样不够清晰,仅隐约可辨,通体环绕着和谐的平行凹凸纹。整体雕琢水平均较前器进步得多。推测两者的雕琢年代亦有不短的差距。
五、两件玉鸟也是文物店的征集品。以青白玉雕琢的一件,平面略近方形。玉料颇佳,总体形态及两翅都保持对称布局,颈部有一道横向凹沟,槽壁陡直底缘平齐宽深若一,截面呈U字形,应属砣具雕琢产物。特别值得注意两侧的对称部位,各有一道纤细挺直的纵向阳纹,更是前所未见之杰作。玉鸟是红山文化发掘品中常见的器种,但在已见到的发掘标本中还没有雕琢工艺如此精良的标本,不能不使人疑虑此鸟的雕琢年代。
六、箍形器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种。虽然外形简单,通体光素没有任何装饰线条,但要掏空内壁形成穿透的大孔腔,在当时决非易事。就剖料成坯工艺而言,它是红山玉器发掘品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如果从单体玉制品的玉料利用系数的角度考察,其利用率是发掘所见红山玉器中最低的一种。但是掏割下来的孔芯仍然可以再次雕琢,从中透露出在总体设计上一材多器共用的高水平琢玉工艺的信息。这也是发掘所得红山玉器所仅见。
这次见到的几件箍形器都保留着一些土锈,但内外壁都没有保留切割的弧线。有幸能亲手揣摩其内外壁之间起伏弧曲度及其走向的变化,还是获得一些新的感受。起初此器之描述往往将横向断面称作椭圆形,以后改作扁圆形似较以前准确。一般说来,古玉的仿制者不一定能见到被仿制的原件,图片及有关文字描述自然成为仿制时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仿琢件是反映仿琢年代对该器认识或研究水平的物化表现。按照这次学习所得的体验,箍形器之体征,除器壁内外不均衡起伏之外,整体形态近似圆角梯形。即自下而上的每一水平横截面,近似不断增大的圆角梯形,不知是否比椭圆形或扁圆形更贴近实际。在近年所见之仿琢器,几乎毫无例外地忠实于椭圆或扁圆的造型。或许在不久之后,很快就有不同截面的箍形器应市,当今如要认真地识别一件传世玉器,除了鉴别者对相应考古标本的研究层次超过仿制者,似乎别无良法。
七、黑龙江省依兰县倭肯哈达洞穴是五十年代李文信先生的发掘成果,所得各件玉器的形状、用料及雕琢风格均近红山玉器。估计该墓地的绝对年代可能晚于红山文化。虽然不能排除出土玉器来自外地的可能性,但在空间坐标上,它们确实落在红山文化分布范围之外,不知是否暂时可称之为红山型(系)玉器。
在沈阳机场临别前,大顺以最新出版的《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相赠,甚喜。这一墓地的绝对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之际,报告书公布了发掘品中包含箍形器(M833:2),勾云形�(M821:5,报告称镂花坠),勾形器(M308:1,报告称雕花坠),臂饰(M659:7),璧(M853:13,报告称璧形坠)和玉�等红山型(系)玉器的线图和黑白照片。其中玉�即多达10件,从照片看豁口似有线切割的痕迹。报告称筒形器“截面为椭圆形”,“筒内侧有摩擦加工痕”,还在线图标出臂饰内臂的弧形雕琢痕迹。这些发掘标本虽然没有见到实物,但能说明以往在殷墟妇好墓及三门峡、侯马周代墓地出土红山型(系)玉器并非偶然,一概将它们当作早期遗留物品处置,看来未必完全妥当。八十年代初,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是我国史前玉器考古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前进,将红山型(系)玉器放到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作深层次的动态考察,应是深入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例如号称天下第一的玉勾龙,在已知诸器中不少是传世品,其中也有仿制品,有确切出土地点的仅有一例,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同类的考古发掘标本。三星他拉出土的标本,整体造型单调,器表也无复杂的装饰花纹,但又显露出秀丽雅洁的神态。有人称之为“雕工精湛,是红山文化中玉雕水准最高的一件”,评价之高似属绝无仅有。此器平面的空间范围,超过540平方厘米,获得并切割如此大面积玉料,而且整体厚薄平直匀称若一,确非易事。直径26厘米的大型玉璧在良渚玉器中已属不可多见之极品。红山玉器中最大的勾云形�长度只有22.5厘米。不论良渚璧还是红山�,玉料两面难免都存在不同的起伏高差。特别需要指出,玉勾龙的玉料利用系数不足原玉料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前面讨论过的箍形器。剩余的玉料固然可以雕琢他件,但箍形器芯还是一块完整玉料,而此类勾龙之剩料至少被分割成三小块,即便在今天,如若事前没有精心筹划一料多用的设计方案,并且掌握得心应手的开料工艺,也不可能如此大胆放肆地处理这样大型的玉料,何况视玉料为神物的史前古人。总观全国史前玉器的考古标本,玉料利用系数如此低小的制品别无他见。也就是说,象勾龙这样以玉材高消费理念设计的开料成坯工艺,在目前已知的史前考古标本中还没有见到过。
此次东北行之前,偶然获得上手观摩一件“天下第一”的机会,虽然不是三星他拉那一件,也可称三生有幸了。此器整体平直匀称,通体各截面弧曲度相若,鬣毛与龙体交接部位呈反向折角,交接部位走向明快和谐,比红山兽形�双耳背后之折角进步得多。鬣毛整体平直,外缘斜杀如刃边,近似红山风格,但两侧弧坡基本保持对称与红山有别。嘴裂、眼缘及顶额部位的网格纹,均用阴线刻表现,嘴、眼之阴线均一端宽深一端尖浅,但阴线两侧呈大致对称的斜段坡,故截面呈“V”字形。只在弯曲部位的坡面呈浅弧形凹曲,近似红山发掘品上打洼工艺。顶额部之网格纹,截面均呈“V”字形。此器之细部若与三星他拉那件标本的照片相比,此器缺少鬣背及斜刃部二处阴刻细线。红山文化的琢玉工艺也有优劣之分,已知的玉勾龙不一定琢于同一年代。仅观一器自然未能涵盖其余各器。但在没有获得确切的考古发掘品证实之前,不将此种器类的时空框架过早地锁定在红山文化之内,不一定不是科学的态度。如将未被正规的考古发掘所验证的传世玉器用作历史研究时,慎重对待,不能不是公正的做法。
我不曾参加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发掘的野外实践,也没有对东北地区史前诸文化有过系统的研究,对于传世玉器更不曾入门。一二次实地学习虽有得益,也只能获得一鳞半爪的知识。管中窥豹在所难免,班门弄斧抑或隔靴搔痒,或两者兼而有之,均属可能。姑记之,用以备忘,日后或有抛砖之效。
(责任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