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以“仁宗”为庙号属于非常高的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以仁宗为庙号的,可谓凤毛麟角,而这其中,又以宋仁宗赵祯最受肯定,可以说,仁宗作为赵祯的庙号,是再恰当中肯也不过了。
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一个“仁”字,已经是对君主最高的评价了。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他的一生,也确实是以宽仁闻名,在正史和宋人的笔记中,关于宋仁宗的宽仁有颇多的记述,比如南宋人施德操在他的著作《北窗炙录》记载过一桩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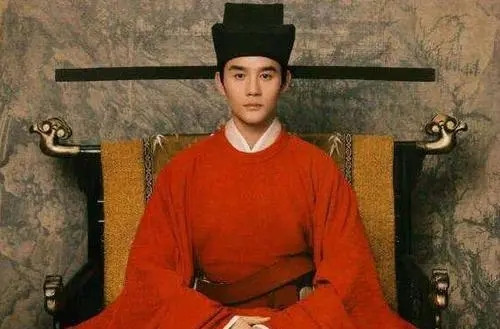
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闻琴铉歌笑之声,问宫人到:“这是哪处的人在作乐?”宫人如实回答说:“官家(指皇帝),宫外头这般的快活,都不像咱宫里如此的冷冷落落啊。”仁宗听这话,却略带自嘲的说:“你可知道,因为我如此冷落,所以他们才能如此快活,我如果要快活,他们便要冷落了”,此言一出,仁宗豁达开明的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真的是难得的千古盛德之君啊。
宋仁宗赵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北宋国力达到了最鼎盛,此时的大宋,称的上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前文提到过仁宗在宫内都能听到宫外的“丝竹歌笑”,当时的汴梁极尽繁华,人流彻夜不息,相比市井的繁华喧闹,宫内却显得的冷冷清清,然而,仁宗并不以宫内的冷清与民间的繁华做对比,而是冷静的意识到正是因为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民间才会变得如此繁华热闹,这对于他来说,正是自己执政成果的表现,因此仁宗反而为汴梁丰富的夜生活感到高兴。
仁宗作为守成之君,虽然没有把大宋推向更高的层次,但是他能守住前三代皇帝辛苦创下的基业,在这中间还使大宋的国力、民生、经济达到了最高水平,其政绩依然得到肯定。仁宗以他的“仁”、“盛德”、“忠厚之政”、“慈俭之德”而受到后人的无数赞美。
仁宗的德与政,配合的完美无瑕,北宋的政治体制,经过太祖、太宗两位皇帝的创制和真宗皇帝的确立,到仁宗在位时,北宋的政治制度已经趋于完善,皇帝与臣子之间和谐的关系及在治国上的完美分工,使得仁宗一朝天下承平,百姓久安。宋仁宗作为一名守成之君最大的美德就是他的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正如《续资治通鉴》所说,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所谓的“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其实是宋代政治制度下形成的治国方式,在儒家,这叫“共治”,在现代,这有些类同于“虚君共和”的意思,即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单看表面,很容易会觉得皇帝的权力是被架空,其实不然,因为北宋的外廷中的三省六部和以“台谏”为名的监察机构,分工是很明确的,三省六部掌国事,监察机构负责监督,而最高决策权在皇帝手上,监管与执政分开,这自然大大减轻了皇帝的压力,所以仁宗才会如此放心的“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时人评价说“仁宗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宋朝称皇帝为官家)”,一个圣明的君主,可以不用“事事恭亲”,“百事不会”也不见得就是昏君,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重要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要如何“做好官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百事不会”反而是君主难得的美德,只要“大事不糊涂”。
作为皇帝,宋仁宗也不是完美的,他也有一个很多男人的通病,即耳根子软,宋朝笔记《曲旧闻》记载过一件事,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出任宣徽使,但在“廷议”时没能获得朝臣通过。张贵妃不依不饶,坚持在仁宗面前吹枕边风,逼得仁宗没办法,一段时间后,仁宗临上朝,张贵妃又一再提醒说“官家,今日莫望了宣徽使”,被催的没办法的仁宗满口答应,于是在朝议直接下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结果跳出来个包拯,以前议张尧佐之事已被否决极力表示反对,而且言语激烈,“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让皇帝很没面子。
然而仁宗并没有当庭暴怒,而是当场收回了成命。回到宫内后的张贵妃,以为事情已成过来拜谢,仁宗却举袖拭面,埋怨到:“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可见,作为台谏的御史中臣,其官秩虽不高,地位却是超然的,这是宋代约束君权与相权的最重要力量,身为皇帝的宋仁宗,面对包拯的直言阻止也不得不妥协。
仁宗虽然耳根子软,少不得身边人给他吹枕边风,但是在大事面前他并不糊涂,这也说明北宋的政治制度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仁宗虽然是皇帝,但他懂得权衡利弊,平衡力量,更会做皇帝,关键时候,绝不能让臣子们下不了台阶,为此宁愿自己回后宫与爱妃吵吵嚷,这样宽仁顾大局的皇帝真是大宋之幸啊。
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告诉了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他在位期间,君臣和谐,百姓拥戴,天下太平无事。宋仁宗对法度的尊重,对君臣边界的遵守都无不让后世啧啧称赞,被称为是“最会做皇帝的皇帝”,正因为宋仁宗的这种皇帝身上难得的美德,才会使他在逝世之后得到举国悼念、“远近皆哭”。





